美聯儲監督副主席Randal K.Quarles:對美國銀行監督演進的思考
美聯儲監督副主席Randal K.Quarles:對美國銀行監督演進的思考
來源 :閑齋自說
前言:如何區分銀行監管與銀行監督?如何解決銀行監管及監督中的透明度?如何改進監督中的一緻性和可預測性?這些問題是現代銀行監管及監督的核心問題。一般而言,監管更多的是指規則的制定,而監督則更多的是指具體的監督執法。當前,監管立法的透明度問題已經在各法域明顯改善,但監督執法的透明度及可預測性相較于前者,則明顯欠缺過多,即使在美國也依然如此。而這也正是制約銀行監管整體效率及穩健的關鍵缺陷。2020年12月11日,美聯儲監督副主席Randal K.Quarles在美聯儲與哈佛法學院和沃頓商學院共同舉辦的主題爲“銀行監督:過去、現在和未來”會議上(通過網絡直播)發表題爲《天眼:對銀行監管演變的思考》的主旨演講,以美國銀行監督的曆程分析了以上問題,并重點就改進銀行監督特别是監督評級框架進行了全面闡述。本人翻譯了該演講,僅供交流。
衷心感謝我們的合作夥伴哈佛法學院和沃頓商學院組織這次會議,并感謝美聯儲工作人員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樣非常感謝所有參與今天活動的主持人和參會成員,以及所有正在在線收看會議的人。到目前爲止,我非常喜歡這次讨論,我希望這次會議将鼓勵更多和更廣泛的有關銀行監管的學術研究。
在許多方面,今天會議的焦點是銀行監管,而不是監管,以及最近學術界對這一話題日益高漲的關注,這些都是值得歡迎的新進展。然而,在其他方面,銀行監管的适當範圍問題完全不是一個新話題。在最近翻閱一些家族報紙時,我偶然看到愛達荷州維克多一家小銀行的總裁埃爾頓·霍爾(Elton Hall)的這句話,1921年11月的《提頓山谷新聞》(The Teton Valley News)援引了他的話:
政府對(我的)銀行的管理如此之嚴,以至于[我]不再知道它的所有者是誰。我被檢查、檢查和複查,被告知、被要求、被限制和被命令……我應該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财源……因爲我不會賣掉我所有的東西,出去乞讨、借錢或偷錢送人,我被咒罵、讨論、抵制、交談、談論、撒謊、挂斷、搶劫和幾乎耗盡,而我執着于生活的唯一原因就是看到地獄的下一步将會發生什麽。
如果霍爾在2020年被送到哥倫比亞特區,他會立即意識到,如果他認爲自己在1921年冬天在愛達荷州的提頓山谷(Teton Valley)被過度欺負,他顯然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但在教堂會衆中的銀行家變得太傾向于同情他之前,我應該指出,我對霍爾有所了解,以及他的名言出現在那些家族文件中的原因,是因爲他的銀行在幾年後就倒閉了,1920年至1930年間,美國近一半的小銀行也倒閉了。霍爾在提頓山脈西坡的銀行被猶他州一位富有遠見的年輕銀行家收購,他的名字叫馬林納·埃克爾斯(Marriner Eccle)。那是在咆哮的20年代,早在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和1933年的銀行業危機之前。在現代監管實踐演變之前,銀行倒閉極爲普遍,即使在繁榮時期也是如此。
那麽,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個新的,但又非常古老的問題呢?我想和今天在座的許多人一樣,首先關注監管(regulation),以此來解脫一些關于其表親監督(supervision)既重要又困難的關鍵問題。
我在美聯儲的目标之一是使我們的監管框架更簡單、更一緻、更可預測和更有效率。這種做法并不新鮮。它借鑒了數十年的實踐經驗和公共政策分析。這種方法最基本的前提是,我們應該不斷挑戰自己,确保我們的政策正在實現預期的目标,這是基于證據和對其對公衆的影響的數據驅動的評估。
這些原則——簡單性、一緻性和可預見性——都與一項或許更基本的監管原則有關,實際上也是法律本身的一項原則——透明度。透明度使監管者的意圖變得清晰,他們的行動對被監管者來說更容易預測。當法規被很好地理解,當它們的可預測性和一緻性建立了對鼓勵遵守法規的公平性的尊重時,法規就會更有效。透明度有助于防範專斷或反複無常的監管。透明度體現在法定程序保護中,例如“行政程序法”中的程序保護,它促進了理解和溝通。
所有這些原則——簡單性、可預測性、透明度、效率——都會帶來更好的監管結果。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更簡單的規則更好,因爲它們更容易理解,更容易被銀行實施,更容易由執法人員監督。可預測、一緻和明确的規則更有效,因爲它們在公司之間和時間上都是一緻的。此外,我們通過公開的叠代過程來制定規則。通過這個過程,我們了解到了潛在的意外後果——這讓我們避免了這些不符合任何人利益的意外。征求公衆意見過程自然也有助于與受規則約束的組織以及任何感興趣的各方進行對話,幫助政府制定一個兼顧收益和成本的監管框架。注重效率有助于确保我們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負擔和外部性。
在全球金融危機(次貸危機)之後,我們依據這些原則建立了新的監管框架。該框架的基本要素——現在包括動态的、對風險敏感的資本金要求以及基于規則的量化流動性标準——都反映了與公衆進行的廣泛而重要的磋商,并仔細分析了這些規則将對個别銀行和美國銀行體系産生的影響。我們的資本充足率基準現在是基于所有銀行的風險和杠杆的标準化度量。此外,每年還會進行一次壓力測試,并圍繞過程和結果進行廣泛的披露,以提供額外的、一緻的風險敏感性。我們現在将流動性監管作爲我們針對大型銀行的強化審慎标準之一,有兩個明确的量化标準——短期流動性覆蓋率(LCR)和長期淨穩定融資比率(NSFR)要求——以及對流動性風險管理的明确預期,這在一項經過公告和評論程序的監管規則中得到了闡述。
在一定程度上,作爲這些改革的産物,我們通過更好地區分風險,提高了我們的監管效率。我們的資本規定要求持有較高風險頭寸的銀行要麽維持應對這些風險的資本,要麽采取措施降低風險。我們的流動性規則同樣要求資金更不穩定的公司持有更多流動資産,或者提高其資金的穩定性。此外,去年美聯儲理事會通過了對我們整體監管資本和流動性框架的修改,以區分個别銀行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在修訂後的框架下,最複雜、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公司受到最嚴格的要求,而複雜程度較低的公司受到不那麽嚴格的要求。從長遠來看,這些變化将帶來更公平、更有效率的結果,同時維護美國銀行體系的安全、穩健以及更廣泛的金融穩定。
由于今年年初實施的監管框架有所改善,銀行在應對COVID事件的挑戰方面處于有利地位。例如,今年3月,美國銀行的客戶從現有信貸額度中提取了近4800億美元,以滿足COVID活動初期收入嚴重中斷期間的現金需求——這是迄今爲止最大的月度增長。銀行能夠在沒有明顯問題的情況下爲這些貸款提供資金,部分原因是利用了新監管體系創造的流動性緩沖。盡管今年早些時候提取了大量撥備,但在這段時間裏,它們不僅維持了資本金,而且實際上增加了資本金。在COVID事件的漫長演變過程中,他們繼續提供信貸,到目前爲止,基本上滿足了經濟中的信貸需求。
當然,擁有清晰、一緻、可預測和高效的監管規則并不是故事的結束。我們的規則不是學術活動。它們代表了對真實的人和真實的企業的具體、有約束力的要求。我們對公衆的義務意味着我們需要審查我們的規則是否得到遵守,發現新出現的風險,并确保任何不足之處得到迅速解決。這是銀行監督者(supervisor)的任務,而不是銀行監管者(regulator)的任務。
監督和監管是不同的任務,我在這段時間裏回顧了我們是如何追求監管的簡單性、可預測性、透明度和效率的,部分原因是爲了說明在監督領域實現這些目标的難度有多大。監管和監督都來自國會授予美聯儲和其他銀行監管機構的法定權力,确立了我們促進安全穩健的銀行體系的職責。監管在普遍的、系統範圍的基礎上做到了這一點。與監管不同的是,監督關注的是公司特有的問題,比如根據我們的法規如何評估公司的特殊風險,以及不容易通過标準化風險衡量方法評估的風險管理框架。例如,雖然我們的資本金規定要求銀行持有特定的資本金水平,但我們的檢查重點放在管理計劃等問題上,以确保它們能夠持續滿足這些資本金要求。監督者以監管評級的形式總結這些檢查結果以及他們對一家銀行的整體評估,我稍後将讨論這一評級的重要性。
我們在監管方面取得的進展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能夠更多地關注監督,以及更簡單、更一緻、更可預測、更有效的監督标準的原則。例如,由于理事會發現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風險管理有了顯著改善,我們從壓力測試過程中剔除了“定性異議”。同樣,我們通過引入壓力資本緩沖(stress capital buffer,SCB)要求簡化了我們的資本框架。鑒于我們現在建立的新的更強大、更全面的監管架構,監督應該如何發展?
例如:在我們從COVID事件影響中脫身後,我們将不再需要維持對大型銀行資本分配的臨時限制,而是可以依賴理事會今年早些時候建立的監管資本框架——壓力資本框架。在它的衆多優勢中,在這個框架下,我們将不再需要審查銀行定期提出的額外資本分配請求。相反,壓力資本框架設定了一個清晰而明确的資本目标,銀行必須在任何時候都保持在高于這個目标的水平。因此,公司可以依賴壓力資本框架的目标來确定他們在任何給定季度可以分配多少資本。這是一個更好的過程,因爲它更可預測,效率更高。
話雖如此,我們可能仍希望對銀行的資本計劃進行有限的審查,以發現壓力測試可能無法完全發現的風險。例如,如果一家銀行進入了一個新的業務領域,但還沒有一個良好的框架來确保其管理者能夠根據其風險來衡量該業務的結果,監督可以檢測到這一缺陷,可以幫助該銀行可以在該未捕獲的風險成爲現實之前解決這一漏洞。同樣,我們新的長期淨穩定融資比率——NSFR——提供了客觀标準,以應對短期融資比率(LCR)之外的風險,從而減輕了監督機構在個案基礎上監控這些風險的壓力。然而,LCR和NSFR并沒有解決流動性風險的所有來源,而糟糕的動态流動性風險管理可能會導緻一家銀行的失敗,就像目前的流動性緊張一樣。通過這些方式,銀行監督可以起到預警系統的作用,在風險演變爲耗盡銀行金融資源或流動性狀況之前識别風險。
然而,與監督實踐同樣重要的是,這些例子也表明,與監管實踐相比,監督本質上更具判斷力、細微差别、自由裁量性、多變性和不透明性。變化無常和不透明會滋生不信任,即使這種不信任根本不值得。這裏的重點是,簡單性、可預測性和透明度帶來的所有好處在監督中都具有同樣價值——但實現監督好處的難度必然要大得多。如果我們不想回到國家的一半小銀行将在我們曆史上最繁榮的幾十年中倒閉的世界,監督的好處是巨大的。
考慮到這一切,鑒于我們對整體監管框架的改進取得了成功,我認爲很自然地會審查我們的整體監管溝通,包括我們的監管評級框架,以考慮如何簡化它,使其更有效率,特别是使我們的評級更一緻、更可預測。我們在監管标準方面已有相當大的透明度?我們公布監管手冊,公布指引,并就最重要的指引征詢公衆意見。我們最近還發布了如何将公司分類到大型機構監管協調委員會(large institution supervision coordinating committee,LISCC)的标準。然而,與規則制定過程相反,爲了适當保護銀行的機密業務信息,絕大多數關于銀行監督過程的溝通都是保密進行的。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當我們發現一家銀行存在重大缺陷,并采取公開執法行動加以糾正時。
監督評級是一個有趣而特殊的案例,因爲它們是保密溝通,但可能會産生公共後果。監督評級是對一家銀行在一個或多個風險領域的實力的保密評估,在某些情況下,是對該銀行面臨的總體風險的綜合看法。評級有一個明顯的好處,那就是總結了一家銀行的整體狀況。在其他考慮因素中,這份評級包括對風險管理的定性判斷,以及對銀行是否遵守适用法規(如資本和流動性要求)的評估。評級還促進了面臨類似風險的銀行之間的比較分析。
監督評級可以追溯到20世紀上半葉,甚至可能更早,當時它們被用來對銀行進行分類,與今天的檢查執法人員給予評級的方式大緻相同。現代版本的評級是1978年國會成立聯邦金融機構審查委員會(FFIEC)的結果。同年,FFIEC建立了“駱駝”(CAMEL)評級體系,以促進對各存款機構統一的審查标準。1979年,美聯儲緊随其後,對銀行控股公司實施了監督評級制度。從那時起,評級就被寫入了聯邦銀行法。特别是,它們在州際分支機構要求以及決定控股公司是否可以從事擴大的金融活動方面發揮了作用。
雖然評級本身仍是機密的監管信息,但美聯儲已采取措施,圍繞評級過程向公衆提供信息。例如,我們用來分配評級的标準一直都是公布的。此外,理事會還就其針對控股公司的評級系統的最新兩次叠代——RFI評級系統和LFI評級系統——征求公衆意見。在過去的一年裏,理事會開始公布監管評級的彙總數據——由不同分組的銀行彙總構成——作爲其銀行監管報告的一部分。
與監督評級有着千絲萬縷聯系的一個概念是,一家銀行是否“管理良好”(well managed)。根據法律,爲了管理良好,一家銀行必須至少擁有“滿意”(satisfactory)的管理評級(如果監管者給予了任何評級),而且一家銀行還必須至少擁有滿意的整體或綜合評級。當《格拉姆-利奇-布萊利法案》(Gramm-Leach-BlileyAct)擴大了擁有銀行的公司可以從事的金融活動的範圍,如證券承銷和保險承銷時,它是在某些條件下這樣做的。要選擇成爲“金融控股公司”并有資格從事這類擴大的金融活動,除其他事項外,銀行控股公司及其主要銀行子公司必須并保持良好的管理。
鑒于這些重大影響,我認爲應該注意到制定規則和作出監督評級之間的過程差異。規則是在公衆完全可見的情況下起草的,在最終成爲最終規則之前有一段征求意見期,聯邦機構有義務爲其規則提供理由。相比之下,監督評級是保密的,并立即生效。銀行不被允許披露這些信息。雖然正如我剛才所說,銀行監督機構應根據已有公布的标準确定這些評級,但總會有一些邊緣個案和千鈞一發的情況,而這些決定都是基於公衆的意見而作出的。
至少有兩個原因說明了爲什麽正确的評級是至關重要的。首先,監督評級是我們與銀行進行的最重要的溝通。它概括了我們對銀行的專家判斷,并讓銀行知道其業績與我們的标準相比如何。其次,正如所讨論的那樣,評級具有實質性的現實後果。評級不令人滿意的銀行與被認爲是令人滿意的銀行相比,面臨着顯著的競争劣勢。如前所述,這些銀行被禁止擴大其金融活動範圍,通常在收購方面将面臨障礙。
自金融危機以來,我們的監督者已經發現了銀行的潛在弱點,并鼓勵它們解決這些弱點。公司現在擁有更強大、更具韌性的風險管理系統。他們能夠更好地識别、衡量和管理風險。這些改進并沒有被忽視。正如我們的監督報告所顯示的那樣,該行業的整體評級軌迹是相當積極的。
我們可以采取一些直截了當的步驟來簡化我們的評級,而不會損害效果。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更簡單的評級框架的模型。适用于我們最大銀行的新框架,LFI評級框架,側重于我們監督重點的三個核心領域:資本、流動性和治理。我們可以考慮對适用于系統性影響較低的控股公司的RFI評級體系和适用于存款機構的CAMELS評級體系進行類似的簡化。在通過評級提高監督效率方面,讓公司更清楚地了解我們是如何應用這些标準的,将有助于促進更有效率的銀行體系。特别是,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我們如何權衡産生評級的各種因素。銀行可能受益,因爲它們将更好地預測監管反饋,并了解它們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來提高評級。監督者可以受益于基于更可預測的标準。
我擔心的是,盡管我們的執法人員使用評級已有近100年的曆史,但我們并沒有一套特别成熟的評級理論——有關内部流程和标準的原則,這些原則有助于我們評估銀行狀況時的一緻性和可預測性。正如我已經讨論過的,人們普遍認爲,評級是銀行監督中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一部分。然而,我們很少有研究或其他實證支持這一結論。這與我提到的一長串監督成就背後的分析形成鮮明對比。舉個例子,我們有一個基于經濟分析的相當好的想法,即一家具有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需要維持多少資本才能提升其安全性和穩健性,但對于如何在滿意評級和不滿意評級之間劃清界限,對我們的标準的支持度并不同樣高。例如,在一家大型全球金融公司,如果該公司另外擁有強大的資本水平,那麽在資本規劃方面,滿意評級和不滿意評級之間應該有什麽區别?我們應該把這條線劃在哪裏呢?我們如何決定死裏逃生,我們默認的平局是多少?
我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麽,我懷疑這會随着情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雖然有一系列定性因素會影響我們的結論,但我們必須從以往的經驗中吸取教訓,提煉出一個假定的答案。這種以分析和證據爲基礎的方法有力地支持了我們的監督框架。我想看看科學能給評級帶來什麽。我認爲,就評級的一緻性和可預測性而言,這可能特别有幫助。由于評級是由人類做出的,而且人類也容易出錯,因此對評級背後的過程更加慎重隻會對我們有所幫助。雖然我們在簡化評級、提高效率、更符合實際監管做法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我希望看到我們的評級方法更加明确和慎重。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和其他審慎監管機構實施了一系列控制措施,以提高一緻性,并支持對評級進行适當的校準(正如我們在内部所認爲的那樣)。我們有适當的工具來監控評級,并檢測其中是否存在任何不尋常的變化。我懷疑還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以運用證據,并确保我們的過程得以促進一緻的結果。
正如我已經提到的,這些努力大多是面向内部的,我們可以從向公衆展示我們的評級是一緻和可預測的努力中受益。我認爲實現這一目标有兩條途徑。其中之一是面向過程和程序的。一種更具實質性。它們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在過程和程序方面,始終存在評級在不同情況下由不同人管理時是否一緻的問題。我想探讨一些評級方法,當這些評級由不同的工作人員在不同的時間點進行确定時,會産生類似的結果。要做到這一點,一種方法是讓評級受到具有不同視角和經驗的多方的審查。這就是穆迪(Moody‘s)、惠譽(Fitch)和标普(S&P)等公共評級機構通過評級委員會進行評級的方式。這就是我們通過LISCC對最大、最具系統重要性的銀行進行評級的方式,在LISCC中,一個包括獨立美聯儲專家的委員會有機會就LISCC類别中銀行的評級提供反饋。設計這一過程,使其對所有銀行都是可靠、一緻和可預測的,是我們應該進一步研究的領域。我們可以探索的另一種方法是,将部分檢查工作用于審查銀行對具體監管标準的合規性,例如我們的一些流動性風險管理标準,這些标準要求适合這種方法。我們将提前承諾,在我們的評級讨論中,給予以上這些評估的結果以特别的權重。我認爲,這種整體模式可能有助于提高監管的一緻性和可預測性,尤其是在标的符合監管标準的情況下。在這種模式下,監管評估由一個有獨立觀點的美聯儲委員會審查,或者至少由美聯儲内部的工作人員在正常評估流程之外進行審查,并在評級時明确考慮了監管标準的合規性。
另一項流程改進涉及監管指導。有時我們發現通過監管指導詳細說明我們的監管标準是有幫助的。一些不容易受到監管的風險領域,比如某些類型的風險管理,也可以從監管指導中受益。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都可以通過邀請公衆就任何适用的指導意見或其他監督标準提供反饋,來提高我們監督過程的可預測性。例如,在最近一項關于資本規劃要求的規定中,我們邀請公衆就我們對各種規模銀行資本分配的監督指導意見提供反饋。最近,我們還就如何處理與治理和内部控制相關的風險征求了意見。我們将繼續尋求對我們指導意見的反饋。所有這些方法都将提高我們評級的可預測性,并提高其合規性。
就向公衆表明評級是一緻和可預測的實質性變化而言,我的目标是盡可能依賴實證分析來指導我們的政策選擇,并在有這種分析支持的情況下對變化持開放态度。作爲監督者,我們應該非常支持将評級更好地理解爲一種評估和溝通工具的努力,以及那些使我們的監督過程具有更多可重複性結果的努力。我們應該鼓勵我們的監督檢查人員和經濟學家圍繞監督評級進行更多的實證分析。例如,最近的一些學術研究表明,評級可以對降低受監管公司的資不抵債風險産生積極影響。我們應該做更多的分析和仔細的審查,以确定是什麽推動了這些結果。
在我們進行這項分析時,我的感覺是,我們應該關注兩個主要變量:我所描述的評級的後果——例如,一家銀行的活動或收購活動被削減——以及這些後果是否相對于導緻評級的情況得到了适當的校準。爲了說明這一點,讓我們回到之前的例子,一家公司在資本充足率的風險管理方面存在缺陷,但通過我們的壓力測試證明自己擁有足夠的金融資源。相比之下,設想一家銀行沒有風險管理缺陷,但其壓力測試結果顯示該公司資本不足。我們對這兩家公司的評估可能是,每家公司都應該得到不滿意的資本評級。
在我看來(我承認,有些人會合理地不同意我的觀點),面臨潛在資本缺口的銀行應該是更嚴重的擔憂。然而,對這兩家公司的基本信息以及評級可能産生的後果——失去管理良好的地位的風險——是相同的。在我看來,這一結果毫無意義。爲什麽客觀上較弱的公司要面臨與客觀上較強的公司相同的後果?
雖然法律規定了不滿意管理評級的最重大後果,但我們有權定義該評級及其校準,以及規定法律未規定的任何額外監管後果。我相信這是非常值得我們花時間來考慮這個校準的。因此,我已指示理事會工作人員研究以下問題:
首先,我們評級框架中定性要素的配置。與定量監管要求相比,在應用這些要素時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權。這些要素傳統上分布在所有評級成分中,包括資本和流動性。這是最好的配置嗎?
第二,如何讓公衆更清楚地了解,作爲監督者,我們如何權衡評級的定性和定量因素。我們怎樣才能最好地傳達這個權衡呢?我們應用的相對權衡是否正确?
第三,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如果有的話)是關于我們新的LFI評級框架相對于我們的RFI評級框架的有效性。例如,從監管溝通的角度來看,LFI評級框架中缺乏綜合評級是否如預期的那樣有益?
如果我們的評級校準不當,我們就有可能在監管方面效率低下。我們還可能提供具有誤導性的綜合評級。盡管我相信,根據我們的書面标準,我們的監督執法人員确實準确而冷靜地對銀行進行了評級,但仔細觀察将有助于識别任何例外情況,以及可能需要改進和改變的地方。
我認爲,美聯儲有責任像評估我們的監管規則一樣,積極評估我們的監督實踐。提供基于經過良好校準、一緻和可預測的标準的評級隻會讓所有人受益。即使我們不改變我們的評級框架,通過評估這一校準過程也肯定會提供寶貴的學習經驗。它還将增強我們對評級框架合法性的信心,以及我們作爲審慎監督者的信心。
謝謝。我期待着接下來的讨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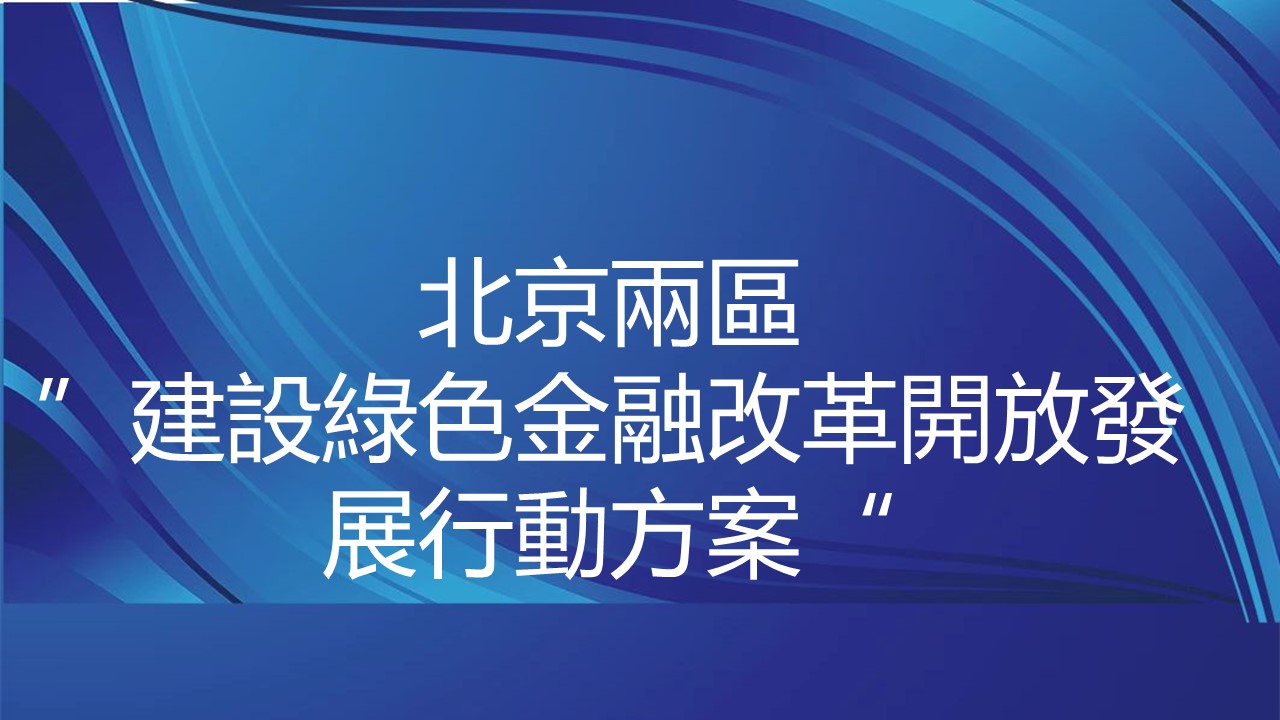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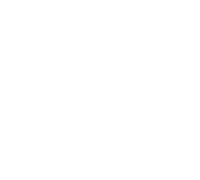




請先 登錄後發表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