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夯實應對氣候變化的數據與計量基礎
周小川:夯實應對氣候變化的數據與計量基礎
最近大家都在學習和領會習主席去年在聯合國大會和氣候雄心峰會上的講話,前不久中央财經委第九次會議研究了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舉措,媒體對這個問題也有大篇幅的報道。我沒有這方面的專長,但跟大家一樣,關心氣候,關心空氣質量,關心環境,所以對這個問題也發表過一些意見。當然,氣候變化問題中碳市場的發展與金融業關聯較多,從金融市場角度出發,我們會比較早就開始關注有關的問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題目是“夯實應對氣候變化的數據與計量基礎”,其中包括:定量問題需要高度重視;需要盡快使總量目标清晰化;打好數據和計量基礎;建立完善的指标衡量和碳市場定價體系。
習主席提出“30·60”目标,指導了我國在碳排放領域的思維轉變。過去在碳排放問題上,我們主要強調發展中國家不能承擔過多義務,發達國家必須給予資金和技術支持,中國因GDP增長快主張使用碳排放強度類相對性指标,對外可承諾增量而不承諾絕對量等。那時認爲,中國人均碳排放不高,累計碳排放在世界上也不算高,說明中國碳排放還有很大的空間。過去的這類想法與習主席提出的“30·60”目标是不一緻的,因爲不管中國GDP增長多快、人均碳排放量多寡,也不管曆史累計量是多少,到2060年都要實現碳中和,也就是淨零排放。雖然2030年前或許還可以有一些數據上的彈性,但後30年就必須按絕對量來規劃和落實,最終達到淨零排放。
2030年的目标明确了碳排放強度減少65%等任務,但排放總量究竟是多少,還不清晰,聽起來各家分歧也不小。顯然年度碳排放的總量規劃尚不清晰,這可能會是出于兩種考慮:一是繼續不使用絕對量指标,可以數字上“打太極拳”,特别是打給外國人看;二是實際上我們自己的基礎數據工作沒做好,沒辦法拿出一緻且可信的數據,并依此進行計量和規劃。
2020年中國的碳排放,多數機構認可并使用的數據大概是100億噸,而2005年并沒有官方或權威公布數字;對未來10年GDP的平均增長率也有不同假設,這樣算下來,各個機構對2030年碳排放峰值絕對量的預測很不一樣,從101億噸到112億噸,各種數字都有。
比如,中金公司最近出的《碳中和經濟學》報告中采用的是2030年中國碳排放峰值爲108億噸,但中金也沒有2005年的準确數據,是根據2017年有關部門公布的當年數字及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了46%推算出來的。另外,中金假定未來10年的GDP增速是年均增長5%,但剛才說的101億噸碳排放峰值也是用GDP年均增長5%來計算的,顯然是由于對2005年基數和口徑(毛排放還是淨排放、二氧化碳還是溫室氣體等)的掌握不一造成的。各家計算的依據不一樣,得出的規劃數據也不一緻,這就需要推敲。
在氣候雄心峰會上,習主席進一步提出了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幾項重要指标: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内生産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将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将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将達到12億千瓦以上。
在這四個目标中,有兩個涉及2005年的基礎數據,但是目前尚未看到官方的或者權威的基礎數據,因此還需要去猜度,或者用不同的假設條件去做推算。人們必然會産生疑問,要麽是數據基礎工作沒做好;要麽是數據透明度不高,不肯給出權威的或者是官方的數字。
如果要按2030年的碳排放強度來安排任務落實,還要考慮GDP的可比性。盡管對未來十年GDP年均增長的預測,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假設,有的用5%,有的用5.5%,也有人用6%,甚至還可以用其它的增長率,但顯然都不應使用名義GDP來計算并比較碳排放強度,用到的應是可比GDP,要與2005年GDP有可比性:可以用GDP平減指數找出可比GDP,或者采用增長率數據,對此不會有什麽分歧。但這裏也需要略加小心,有時候增長率的年初數據(初步核算數)、初步核實數、最終核實數以及普查後修正數差距會很大(特别是2005、2006、2007年),比如2007年GDP增速的初步核算數、初步核實數、最終核實數以及普查後修正數分别是11.4%、11.9%、13%和14.2%,之間居然相差2.8個百分點。如果用的不是可比數據,計算出來的碳排放強度差距就會很顯著。此外,如果用減排強度來衡量目标的話,隻要GDP增長率數字上去,就會給中國2030年繼續多排放提供很多彈性空間。
有人提出疑問,如果有關部門已經掌握2005年以來中國碳排放強度的下降比率,且期間GDP增長率或平減指數相對而言又比較可靠,則有關部門不可能不知道2005年碳排放總量。否則碳排放強度下降46%(2017年相比2005年)的報告數是怎麽得出的?顯然這是矛盾的。
從技術上講,如果沒有年度總量數字,減排任務怎麽分解?效績如何考核?碳市場定價又怎麽形成?顯然都存在無解的問題。此外,總量數字明确,也涉及未來40年整個減排進程的動态安排,整體安排上是前快後慢、前慢後快還是平均推進,該如何達到優化的選擇,等等。
此外,也需要評估過去15年(2005到2020年)中我們究竟有多大進展,在減排方面做出了哪些成績,未來10年(2020年到2030年),我們又希望安排多大的進展,減排的落實是否及如何得以加強。
總之,不管從規劃角度還是實際工作進度來講,如何選擇優化的進度安排(前松後緊還是前緊後松),首先必須把數據基礎、計量基礎和分析基礎做實,特别是總量目标要清晰。
那什麽是最大頭呢?大家都知道是發電行業,其碳排放占比世界平均看是41%,中國還要高,大概是52%。未來我們還會多用電,少用化石能源,也就是通過用電來替代直接的化石能源,同時将發電轉化爲綠色電力或者是零碳電力。有人測算到2060年電力占比将達70%甚至更高。因此電是“最大頭”,電力行業如果沒抓好,再怎麽抓其他行業,碳減排最終目标也完不成。
習主席在氣候雄心峰會上提出,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将達到25%左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将達到12億千瓦(也就是1.2TW)以上。據報道,2019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占的比例約15%,到2030年要提高到25%,這是既艱巨但也不是離譜的目标。
從裝機容量上看,我們現在風電、光電新裝機容量大概是0.056TW,如果提高50%,也就是平均新裝機0.084TW,10年下來就裝到0.84TW,加上現存累計裝機0.41TW(2019年的數字),就達到1.2TW。這也不是太艱巨的任務,因爲設備制造和安裝能力上來了,而且價格也慢慢變得有競争力了。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一部分分析人士對電力行業減排轉型給出了過分樂觀的看法,忽視了非化石電源及輸配電的技術難度。雖然說風電、光電技術的提高已顯著降低了裝機和運行成本,但真正提高其在發電總量中占比不僅靠裝機進度,還有待于多項研發與技術的提高,不能簡單化地把電力行業的綠色溢價估爲負值(即過分樂觀)。
裝機容量要通過年均發電小時及電網接納能力的數據分析,把裝機容量變爲年度發電量供給。在這裏不同發電設備的年均發電小時數就變得非常關鍵。我給非電力專長的經濟學者一組輪廓性的概念(爲方便記憶,數字作了近似),光電年發電小時數大約是1500小時,風電是2500小時,水電是3500小時,煤電或者火電主力是4500-6500小時,核電是7500小時。可以看出不同發電來源的年均發電小時差别是很大的。中國的實際數還略小于這組數,目前中國光電的年均發電小時數還不到1300小時,光照弱的地區連1000小時都到不了;風電實際上也隻有2100小時左右;火電可以高達6000小時以上,但目前中國實際上火電年平均還沒到4500小時,才4200小時。因此,光電和風電,即便裝機容量上去很快,它在總發電量中占比還是不能高估。
另外,由于是間歇式發電,需要比較高的電網技術、電網水平和儲能設備,尤其是儲能,可能還要取決于未來科技的發展。
在我國,風能和光能豐富的地區(年均發電小時高于均值)往往不是人口和産業聚集地區,需要長距離輸電,盡管超高壓輸變電技術已較成熟,但建設成本的攤入和線損成本(目前約6%)也是不可忽視的。這一類技術上、經濟上的因素與電網運行中的棄風、棄光現象有内在聯系。因此,并不像有些同志那樣樂觀,看到風電、光電裝機容量上升很快,就說中國有底氣率先實現目标。事實上任務還是很艱巨的,風電和光電在實現“30·60”目标中發揮作用還要大量依靠研發和投資,不能把事看得太簡單。
重視發電行業減排,尤其需要削減煤炭。中國對煤炭的依賴率太高,削減化石能源,首先是要削減煤炭。這裏面有一個數字值得關注。今年兩會期間煤炭協會發布報告說“十四五”末期中國煤炭年産量将控制在41億噸。這是什麽概念呢?2012年中國煤炭年産量達到39億噸,後面略有減少,2020年又回到39億噸。如果到2025年的5年規劃期末還打算再增加1億多噸,這個數字不太令人鼓舞,會使得後面的削減任務非常艱巨。
這裏面或許存在一種可能,那就是在“十四五”規劃制定過程中,可能還沒來得及理解習主席在聯大及氣候雄心峰會上的講話精神,因此“十四五”規劃中的碳減排或者說溫室氣體減排方面的目标和内容較弱,不飽滿。這些指标和落實内容是不是需要再研究,是值得考慮的。
剛剛談到了從裝機容量轉換到發電量,接下來再談談新增裝機容量所需的投資資金量,即多大的投資才能達到所需的裝機容量,這裏主要包含裝機成本,但電網、儲能、調峰、輸配電投資成本也是絕對不可忽視的。如果隻看裝機成本的數字,很容易受到鼓舞,因爲風電、光電裝機成本已降到比較低,比火電和核電低。核電是最貴的,但核電投産後一年會發電7000多小時。目前,火電的投資回報率仍是最具競争力的,但如大幅減排,可能需要CCS(碳捕獲與存儲)設備及投資,投資成本顯著上升。
此外,CCS運行成本也很高,會使廠用電大幅上升約20%。當然,CCS技術上還不成熟,有待發展,中國需要特别關注并加以支持。這些都要放入對電力行業未來投資量的測算裏面,隻算新型電源的裝機成本顯然是不夠的。然後要問,電力方面的新投資未來是靠什麽回收?如果僅靠供電收入本身的回報是不夠的,就必須靠碳市場(或者碳稅)來補充,才能有足夠的激勵機制,從而吸引足夠的投資進來。
此外,從行業結構來看,中國過去習慣用生産法說第一産業碳排放多少,第二産業碳排放多少,第三産業碳排放多少,中國第二産業碳排放特别多,在電力使用中占比近70%,這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這種劃分方法與國際上是有差别的,導緻不太好作國際比較。歐美的碳排放第一大行業是發電,第二是交通,第三是建材(含建築鋼材)與保溫。如果在電力、交通和居住三組分上下大功夫的話,80%以上的碳減排問題可以得到解決。
這種劃分方法強調了人類居住的耗能和碳排放,人類居住需要建築、城鎮化、一部分基礎設施及保溫(供暖及制冷),從而需要大量鋼材、水泥、鋁材,這三項的碳排放占了第二産業生産方排放的多一半,爲此要相當重視。如果把居住有關的大部分排放放在第二産業裏,容易有誤解和誤導。
當然,正如前面所說,鋼鐵和建材行業将來應大量使用清潔電力和綠氫,而放棄現在燒煤、油和氣的生産工藝,進而把減排負擔轉移到發電業,因而電力行業的綠色改造更重要。此外,中國正處于城市化大幅向前跨進的階段,對于建築保溫性能的重視程度還不夠,未來建築保溫問題也會在碳排放中占據不小的比例。總之,結構方面要弄清楚才能做優化,這也需要大量的基礎數據、參數及大量計量,并相應設計好各項指标體系,以提供合理且充分的激勵機制。
碳減排後可能會影響GDP,影響通貨膨脹,影響經濟增速,對此問題該怎麽看?GDP是流量,财富是存量,該如何看待碳中和與這二者之間的關系?
從流量的角度,有一句話叫“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需求可以不斷地更新,流量就能維持或者增加,就像一些人不管穿不穿,總不斷地買新衣服,衣櫃裏挂了一大堆,GDP就上去了。
從這個角度講,發電原來用煤電,設備的壽命還未用足,現在就要改成風電、光電、核電,顯然有些浪費,但這一更換,需求就上去了,供給上又有潛能,實際上起到增加GDP的作用。歐洲人就很強調這一點。即便說假如現在判斷失誤,事後發現溫室氣體效應的理論是錯的,或許威脅沒那麽大,那麽減排不就白幹了嗎?就像買了衣服而根本沒穿過,雖然GDP增加了,但這種GDP增長會産生浪費,沒有積累财富。
舉個例子,我們不少農民工到城裏打工,掙了錢回家蓋房子,蓋了房子也不怎麽回去住,過了十年又拆了蓋新的,這就相當于沒有多少财富積累。歐洲很多房子都是一兩百年前蓋的,甚至更久,現在還接着用,這就體現财富積累;還有一些财富甚至可以升值,比如藝術品。
所以,即便氣候變化理論搞錯的話,用風能、光能把化石能源給提前淘汰了,GDP會因此往上走,但财富并沒有得到積累。這就涉及财富和GDP的關系。有人隻說碳減排會造成大量浪費,對此應當從經濟學的流量和存量角度來予以準确把握。更重要的一點是,财富的計量也是有難度的,而習主席關于金山銀山的論點說的就是财富,未來對環境和氣候的财富估值會遠遠大于荒廢火電廠造成的财富浪費。
其實,真正難權衡的是,在碳減排過程中生産和生活的投入成本提高了,可能影響了産出競争力以及供需關系,有可能因爲通貨膨脹過高造成經濟衰退,所以需要把握好碳減排的進度,把握好創造GDP流量需求與成本控制之間的平衡點。說到競争力,如果全球能共同切換能源結構,則相對競争力的變化是不顯著的。如果不大緻同步,就會産生各種顧慮,有人會測算碳腳印(Carbon Footprint)并主張據此征收邊境調節稅。
金融中大量的業務實質上就是管理和控制風險。在氣候變化方面,金融方面現在最大的風險就是,如果不重視減排,可能造成投資失誤,有些在建項目中途會被叫停,或者未來因價格調整、人們思維改變、産品會提前停用等,導緻原來認爲能盈利的項目變爲不盈利甚至虧本。對這類氣候變化引發的風險要高度重視,比如建設電廠,要按20、30年甚至更長時間來算賬,這當中有關碳減排的配額、價格、政策都需要預測,财務上就很可能出問題。這是微觀層面的風險控制。
還有一類是宏觀上的風險控制,涉及GDP、财富、全經濟的效率、競争力,很多測算都是概率性的,包括氣候變化理論對錯的風險。處理這類問題,有一種權衡辦法,就是貝葉斯決策。未來各類事件的出現是有概率的,氣候變化理論也是這樣,理論站得住腳的概率可能高達90%以上,但也還有較小的可能性說氣候變化威脅并不存在,隻是虛驚一場。到目前爲止,國内外也還有一小部分科學家強烈反對氣候變化理論。
經濟學家不是這方面的裁判員,但可以用所謂的“專家法”對未來的狀态賦予概率,各自對應其有多大可能是對或者錯,以及各對策對應的經濟社會總收益或總損失,然後基于此進行經濟決策和風險管理,這就是貝葉斯決策。當然,這種分析與決策均建立在良好的數據與計量基礎之上。
過去曾在講述貝葉斯決策時舉過轉基因的例子,這是最典型的應用實例。一方面,轉基因存在某種小概率,有可能對人類生命、繼承等存在重大威脅;另一方面,轉基因技術較爲肯定地提高糧食産量,解決或者緩解了土地短缺、糧食安全、進口糧食依賴、城鎮化用地缺乏、房價高企等其它方面的問題。對此可以分别運用相應的概率值,對戰略選擇進行風險衡量和抉擇。這是典型的貝葉斯決策。中國作爲人口衆多、人均耕地很少的國家,與歐洲很不一樣,風險控制加權的戰略選擇就會與歐洲有差異。
當前全球在許多方面尚缺少共識,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氣候問題上也有争議。習主席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地球村的高度,在氣候變化方面作出了鄭重承諾;美國也決定重返巴黎協定,圍繞氣候變化問題的讨論可能會進入一個新階段。
但有一些具體問題還存在解不開的争議:發展中國家普遍都認爲,發達國家對減排的資金和技術支持遠遠不到位;存在跨境碳排放問題,也就涉及貿易的跨境調節稅,還有跨境飛機、跨境船舶等在國際領域内的碳排放問題。
現狀是,對跨境碳排放應予以調控,這相對比較易于達成共識;但收稅或收費應進誰的口袋則争議巨大。現有的國際體制和多邊機制難以應對,争搶很容易炙熱化,有人形容說,像保衛領土主權一樣,寸土不讓,打起來也不見怪。這樣的問題不易達成共識,還談不上采取共同行動,使得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可信度受到質疑,因此需要真正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多邊主義的宗旨,以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構建布雷頓森林體系爲參考模闆,大膽設計,大力推動。
碳市場涉及很多問題,我在别處也談過,包括需要有總量目标,可采取有配額的一般均衡模型進行分析等。今天主要想說碳市場的用途導向。一種說法認爲,其用途主要是調節即期的供求關系,也就是讓碳排放多的要在當期盡量“勒一勒褲腰帶”,花錢購買排放權。但實際上受制于當期技術和設備性能,供求平衡有衆多剛性因素,很多減排任務在當期或短期内是調節不動的。
我認爲,碳市場最重要的作用是引導投資,通過跨多個年度的項目與技術投資,着重改變未來的生産模式和消費模式。實現“30·60”目标的過程必然要依靠大量投資,無論是發電、交通等行業的碳減排,還是發展新科技,都需要新的投資。
那到底要多少投資?中金公司的《碳中和經濟學》報告預測,到2060年中國總綠色投資需求折合現在的币值約爲139萬億人民币。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2021年3月公布報告中指出,2050年之前,全球規劃中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必須增加30%至131萬億美元,按照目前全球碳排放中國約占比三分之一和當前彙率簡單估算,中國就需要大約283萬億人民币的投資。
能否吸引到這麽多投資,這麽多的投資如何引導好、激勵好,不釀成大虧空,顯然是件大事、難事。這麽大量的投資不可能憑空而來,也不會憑号召就能實現,每項投資都需要導向,需要算賬,而算賬就必須有依據,需要碳市場給出信号,涉及大量與碳價格、研發風險投資有關的基礎數據和投資計量。如果既無總量信息也無碳價格信息,是很難讓人真正下決心投資的。
同時,未來的新科技産生以後,也要依靠碳市場評估其效果。因此如果僅僅把碳市場看作是取得當期平衡的現貨市場,将會犯很大的錯誤,必須把碳市場看作是主要引導跨期投資的金融市場,是主要用來引導中長期投資的市場。此外,中國主管部門曆來是各管一攤,因此,碳市場由哪個部門建設管理,也值得關注。總之,碳市場是一個涉及綠色治理的問題。
最後還要回應一下開頭所講的,碳減排問題時不我待,現在就應當高度重視起來;同時,讨論這些問題,需要建立在紮實的數據計量和定價的基礎之上。以上就是我與大家分享的對碳中和“30•60”目标這的一些看法,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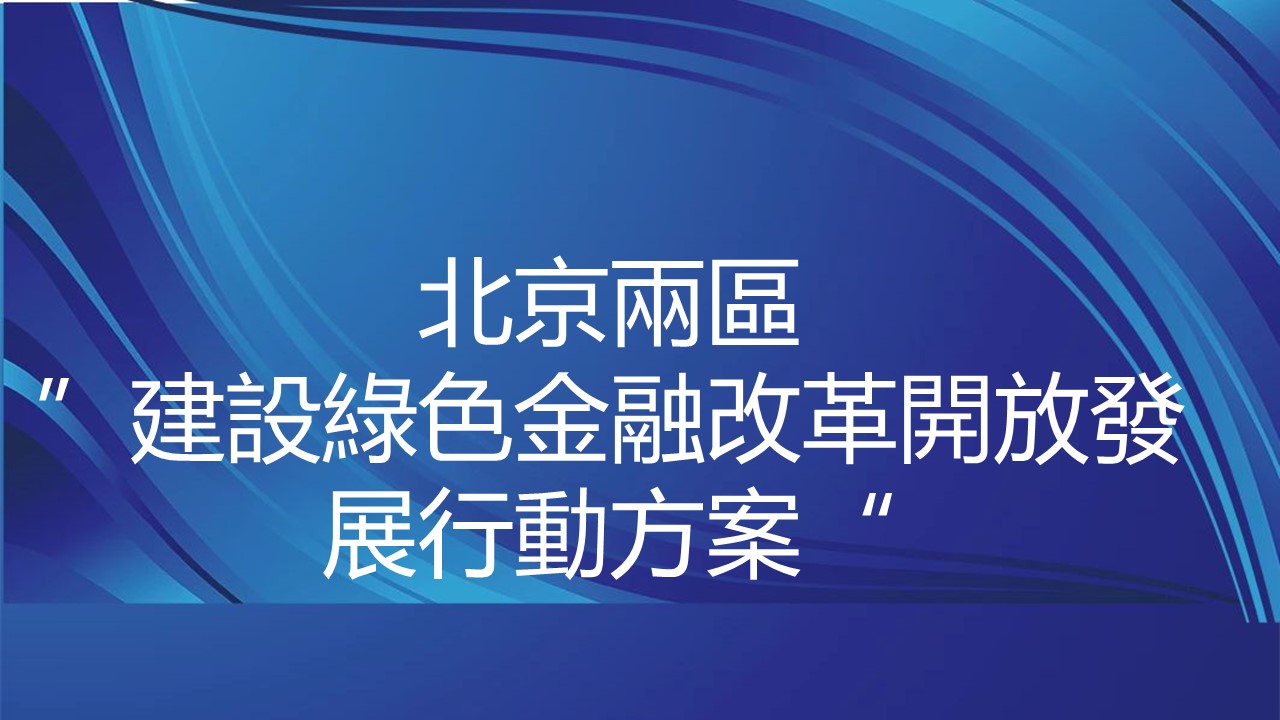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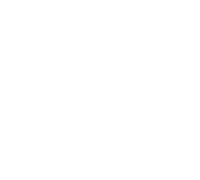




請先 登錄後發表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