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磊:七普人口數據簡評
郭磊:七普人口數據簡評
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第一,首先需要指出一點,普查數據、小普查數據、年度數據口徑不同,不可混用。普查數據10年一次,我們可以把它簡單理解爲“存量數據一次性修正”。比如按2020年底總人口的141178萬,比2019年底增加1173萬(正常年份每年增加400-800萬)。實際上,這普查年的1173萬并不是2020年一年增加的,它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存量數據統計的修正。
第二,存量人口的141178萬,以及2020年比2010年增加7206萬(2010年比2000年增加7389萬),這兩個數字都超出前期市場過于悲觀的預期。過去10年淨增加人口幾乎持平于再往前10年(隻少了183萬)。當然,這很大程度上與2016、2017年二胎政策所帶來的短期人口脈沖有關。2017年之後新生兒人數逐年下降的趨勢還是十分明顯的,增量形勢仍比較嚴峻。
第三,2020年新生兒1200萬,環比2019年下降18%左右,基本符合預期。前期已經公布的公安部戶籍登記數據是較2019年下降15%左右。
第四,2020年新出生人口的下降是三個因素的疊加,一是疫情影響,産檢醫療條件的變化、收入預期的變化和未來不确定性的上升導緻推遲生育計劃,對2020年來說,全球出生率曆史新低的情況比較普遍。二是育齡人口的代際下行,即由于生育政策影響,1987和1990年之後新生人口曾出現兩輪明顯下行,這對應2017年後育齡女性人數的變化。三是“工業化-生育率悖論”。生育率的下降幾乎是工業化國家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
第五,簡單來說,第一個因素代表“生育條件”,屬短期擾動,估計主要影響2020-2021年;第二個因素代表“育齡基數”,需要及時、迅速進行政策調整,否則下一個階段壓力會進一步加大;而第三個因素代表“生育意願”,它作爲一個全球難題的規律性被很多人所忽視。但恰恰是這種規律性意味着挑戰會更大。它可能和一系列内生原因有關,如現代社會體力勞動邊際回報率的下降、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上升、住房和教育成本的上升等,對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還有一個原因是流動人口比例偏高,年輕人會面臨“打工-返鄉-結婚-生子”、“城市就業-買房-結婚-生子”這樣兩種典型路徑,均會導緻婚育年齡偏晚,從而帶來生育率的變化。
第六,從這個框架去理解,要影響人口曲線,一則要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二則主要還是有針對性的瞄準“工業化-生育率悖論”,比如通過一系列組合政策降低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通過降低住房成本、教育成本、提升教育資源可得性來降低年輕人生養育的成本預期;通過更廣泛的城市群建設,推動工作機會的區域多元化,降低因人口流動模式固化導緻的代際晚育的現象。
第七,老齡化特征繼續上升,65歲以上人口比重達到13.5%,上行速度也比上一個十年更快。從世界銀行口徑數據看,全球65歲以上人口比重大約在9.1%左右,高收入國家這一比例爲18.3%,中等收入國家爲7.8%。老齡化對經濟結構、産業結構都會産生深刻影響。
第八,本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口已有2.18億人,較2010年的1.19億大幅增長。和2010年相比,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爲15467人。這一點是“工程師紅利”形成的基礎。
正文
首先需要指出一點,普查數據、小普查數據、年度數據口徑不同,不可混用。普查數據10年一次,我們可以把它簡單理解爲“存量數據一次性修正”。比如按2020年底總人口的141178萬,比2019年底增加1173萬(正常年份每年增加400-800萬)。實際上,這普查年的1173萬并不是2020年一年增加的,它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存量數據統計的修正。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全國人口共141178萬人,與2010年的133972萬人相比,增加了7206萬人,增長5.38%,年平均增長率爲0.53%。
我們需要簡要了解普查口徑和年度口徑的關系。
根據國務院2010年頒布的《全國人口普查條例》,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位數逢0的年份爲普查年度;在兩次人口普查之間開展一次較大規模的人口調查,也就是1%人口抽樣調查,又被稱爲“小普查”。在不進行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樣調查的年份進行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
不同口徑的數據是不可直接混合計算的。
比如2016年初,統計局公布的2015年總人口數爲137462萬人;而2016年4月20日《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公布的“小普查”數據顯示2015年人口總數爲137349萬人 。
存量人口的141178萬,以及2020年比2010年增加7206萬(2010年比2000年增加7389萬)這兩個數字都超出前期市場過于悲觀的預期。過去10年淨增加人口幾乎持平于再往前10年(隻少了183萬)。當然,這很大程度上與2016、2017年二胎政策所帶來的短期人口脈沖有關。2017年之後新生兒人數逐年下降的趨勢還是十分明顯的,增量形勢仍比較嚴峻。
2020年人口總數爲141178萬,比2010年普查數據的133972萬增加7206萬,這兩個數據都是超前期市場悲觀預期的。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比2000年增加爲7389萬。
過去十年人口增長的7206萬比2000至2010年的7389萬隻減少183萬,這在一定程度上應歸于2016、2017年二胎政策放開背景下的短期新生人口反彈。
2016年、2017年新出生人口分别爲1786、1723萬,比2010-2015年年均值高了110萬左右,比2000-2010年的年均值高了126萬。
2017年之後,新生兒數據下降比較明顯,2018年、2019年、2020年分别爲1523萬、1465萬、1200萬。
2020年新生兒1200萬,環比2019年下降18%左右,基本符合預期。前期已經公布的公安部戶籍登記數據是較2019年下降15%左右。
國家統計局局長甯吉喆5月11日在發布會上表示,2018年以來出生人口數量有所回落。初步彙總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爲1200萬人,這個規模依然不小。
1200萬是确切數還是約數尚待詳細數據,按照1200萬,則環比2019年下降18%左右,大緻符合預期。
2021年2月8日,公安部戶政管理研究中心發布《2020年全國姓名報告》,報告顯示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經到公安機關進行戶籍登記的新生兒共1003.5萬。2019年同一口徑數據即戶籍登記的新生兒數爲1179萬 。這意味着這一口徑下2020年新生兒下降15%左右。
2020年新出生人口的下降是三個因素的疊加,一是疫情影響,産檢醫療條件的變化、收入預期的變化和未來不确定性的上升導緻推遲生育計劃,對2020年來說,全球出生率曆史新低的情況比較普遍。二是育齡人口的代際下行,即由于生育政策影響,1987和1990年之後新生人口曾出現兩輪明顯下行,這對應2017年後育齡女性人數的變化。三是“工業化-生育率悖論”。生育率的下降幾乎是工業化國家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
第一個因素是疫情影響,在前期報告《人口趨勢及疫情影響》中我們指出: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出生率在2020年均出現顯著下行,出生率曆史新低的情況比較普遍。疫情影響出生率主要源于産檢醫療條件的變化、收入預期的變化和未來不确定性的上升導緻推遲生育計劃。數據顯示疫情導緻較大比例歐洲育齡夫婦推遲育兒計劃。另一個可參照案例是2003年非典疫情,北京地區出生率曾從2002年的6.6‰大幅降至曆史最低點的5.1‰。考慮到新冠疫情對年初的影響會落在2020年,二季度起的影響主要落在2021年,2021年出生率數據可能會繼續偏低。
第二個因素是育齡人口的代際下行。由于國内出生人數在1987年是一個高峰,1987和1990年之後曾出現兩輪明顯下行,這對應2017年後育齡女性人數的變化以及這輪新生兒人數的快速下降。
第三個因素是工業化-生育率悖論。這幾乎是工業化國家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需要對這一過程的艱巨性有充分預期。比如韓國粗出生率已從1980年的22.6‰降至2018年的6.4‰,印度粗出生率已從1980年的36.2‰降至2018年的17.9‰,越南粗出生率已從1980年的31.9‰降至2018年的16.8‰(相當于中國1996年前後水平)。歐美下降較慢,但同樣處于下行趨勢中,美國1970、1980、2018年分别爲18.4‰、15.9‰、11.6‰;德國同時段分别爲13.4‰、11.1‰、9.5‰。
以總和生育率來看,1990年美國、韓國、印度、越南分别爲2.1、1.7、3.6、3.6,2018年則分别爲1.7、1.0、2.4、2.1。總和生育率顯著偏高的國家,如尼日爾、索馬裏、剛果(金)、馬裏、乍得、安哥拉、布隆迪、尼日利亞,均屬前工業化國家。
簡單來說,第一個因素代表“生育條件”,屬短期擾動,估計主要影響2020-2021年;第二個因素代表“育齡基數”,需要及時、迅速進行政策調整,否則下一個階段壓力會進一步加大;而第三個因素代表“生育意願”,它作爲一個全球難題的規律性被很多人所忽視。但恰恰是這種規律性意味着挑戰會更大。它可能和一系列内生原因有關,如現代社會體力勞動邊際回報率的下降、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上升、住房和教育成本的上升等,對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還有一個原因是流動人口比例偏高,年輕人會面臨“打工-返鄉-結婚-生子”、“城市就業-買房-結婚-生子”這樣兩種典型路徑,均會導緻婚育年齡偏晚,從而帶來生育率的變化。
“工業化-生育率悖論”可能和幾個因素有關:
(一)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生活目标更爲多元化;
(二)是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随農業、手工業在經濟中的比重下降,體力勞動對家庭财富的邊際回報下降;
(三)女性的人格和職業更加獨立,勞動參與率上升;
(四)住房、求職和教育成本上升,導緻生育、養育的成本大幅上升。
(五)養老體系逐步形成,養子防老的功用下降。
對于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流動人口比例偏高,年輕人會面臨“打工-返鄉-結婚-生子”、“城市就業-買房-結婚-生子”這樣兩種典型路徑,均會導緻婚育年齡偏晚,從而帶來生育率的變化。還有就是女性勞動參與率尤其偏高。
所以,出生率和生育率下降具有内生性,對這一過程艱巨性要有充分預期。
從這個框架去理解,要影響人口曲線,一則要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二則主要還是有針對性的瞄準“工業化-生育率悖論”,比如通過一系列組合政策降低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通過降低住房成本、教育成本、提升教育資源可得性來降低年輕人生養育的成本預期;通過更廣泛的城市群建設,推動工作機會的區域多元化,降低因人口流動模式固化導緻的代際晚育的現象。
政策似乎也已在框架上瞄準這兩個方向。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實際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十四五”規劃建議稿指出“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未來相關政策值得關注。
老齡化特征繼續上升,65歲以上人口比重達到13.5%,上行速度也比上一個十年更快。從世界銀行口徑數據看,全球65歲以上人口比重大約在9.1%左右,高收入國家這一比例爲18.3%,中等收入國家爲7.8%。老齡化對經濟結構、産業結構都會産生深刻影響。
普查的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達到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13.50%。2010-2020年,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個百分點。與上個十年的2000-2010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個百分點。老齡化進程有所加快。
本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口已有2.18億人,較2010年的1.19億大幅增長。和2010年相比,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爲15467人。這一點是“工程師紅利”形成的基礎。
本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擁有大學(指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爲218360767人,而2010年這一人口數爲119636790人;擁有高中(含中專)文化程度的人口爲213005258人;擁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爲487163489人;擁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口爲349658828人(以上各種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類學校的畢業生、肄業生和在校生)。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爲15467人;擁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上升爲15088人;擁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8788人下降爲34507人;擁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由26779人下降爲24767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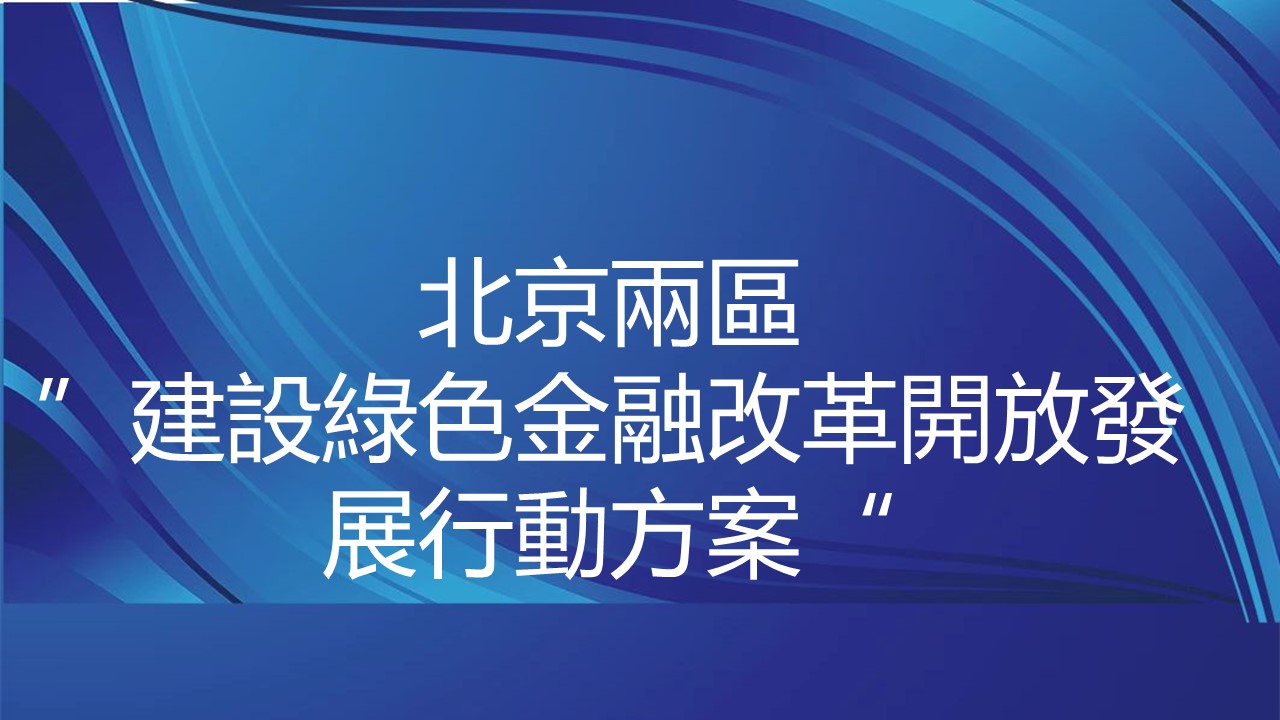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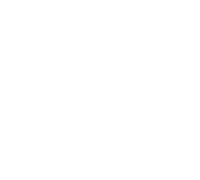




請先 登錄後發表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