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爲什麽各國央行都越來越偏愛數量調控
盛松成:爲什麽各國央行都越來越偏愛數量調控
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最近十幾年來,中央銀行似乎更加偏愛數量調控工具。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今年的傑克遜霍爾會議講話中,重申美聯儲将繼續保持現有資産購買的速度,并提出如果經濟的發展大緻符合預期,今年可能開始Taper。這些都是比較典型的數量調控措施。鮑威爾尤其強調了Taper與加息并無必然聯系。美聯儲9月議息會議依然保持聯邦基金利率(0-0.25%)、準備金利率(0.15%)和隔夜逆回購利率(0.05%)不變。爲什麽美聯儲對于利率變動如此謹慎?數量調控似乎正在成爲央行的主要工具,這與過往相當長時期内主要央行倚重價格型調控(即調控利率)、以泰勒規則爲貨币政策的制定依據很不相同。
理論上,量與價是一個硬币的兩個面。但在經濟實際運行中,自然利率是一個難以觀測的變量,這增加了利率調控的難度。而央行以“有形之手”操控貨币政策,其決策更是面臨着信息有限的制約。數量工具靈活性、可控性較高,更适合複雜情況下的需要,而利率傳導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央行較難把控。我們認爲,這是央行越來越偏愛數量調控的一個重要原因。從深層次講,貨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關系正在發生轉變,從相互替代到互爲補充,央行也因此更加倚重數量調控工具。
央行“有形之手”對經濟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市場上也不乏對央行主動幹預市場的反思和批評,甚至有觀點認爲,央行本身已經成爲金融不穩定的一個根源。從國際金融危機到新冠疫情沖擊,宏觀經濟金融調控的實踐不斷面臨新的挑戰,但新的理論研究和政策框架尚付阙如。面對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央銀行隻能“摸着石頭過河”。
一、近年來央行數量調控的主要特征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開始,全球主要經濟體幾乎都開啓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貨币寬松。美聯儲先後進行了四輪量化寬松,其資産負債表規模從危機前的不到9000億美元大幅擴張至4.5萬億美元。日本則實施了直接以增加基礎貨币爲目标的“質化和量化寬松貨币政策”(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onetary Easing ),其基礎貨币規模由2012年末的138萬億日元擴大至2014年末的270萬億日元。日本央行更早的量化寬松則始于2001年3月,這是爲了應對當時日本面臨的通貨緊縮和低利率困境,在零利率下對抗通縮和經濟下滑。這也是貨币政策首次使用量化寬松的實踐。量化寬松既是零利率約束下不得已的選擇,也開啓了貨币政策調控的新篇章。
無論是當年的危機,還是近在眼前的新冠疫情,數量型調控都是央行應對經濟沖擊的主要手段。疫情沖擊開啓了世界範圍内新一輪量化寬松。據《經濟學人》雜志預測,發達國家央行的資産負債表總規模到2021年年底将達到28萬億美元,其中約五分之二來自疫情期間的量化寬松政策。
除了數額巨大的流動性投放外,央行流動性工具的創新也很頻繁。美聯儲新創設的向金融機構和貨币市場融資的主要政策工具基本都是以數量工具爲主的,例如面向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定期拍賣便利(TAF)、面向一級交易商的短期證券借貸工具(TSLF)和一級交易商融資便利(PDCF)、面向票據發行機構的商業票據融資便利(CPFF)、面向貨币市場投資者的貨币市場投資者融資便利(MMIFF)等。其中,一級交易商融資便利允許一級交易商像存款類金融機構那樣通過貼現窗口借款,其利率是固定不變的,而資金數量取決于交易商的需要。這是典型的數量型調控。而且美聯儲不需要預設一級交易商融資便利的流動性投放規模,完全根據市場的實際需要提供資金,這是傳統的利率調控無法做到的。
此外,數量調控工具的創新還大大擴展了央行提供流動性的範圍,流動性投放的針對性、精準性更高。美聯儲的流動性支持對象不再局限于銀行,而是面向各類金融機構、特定金融市場(如商業票據市場)以及實體經濟。美聯儲還通過央行間流動性互換,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動性,實質上扮演了全球央行的角色。
二、利率調控的局限性與貨币政策面臨的新環境
首先,價格型調控受到零利率的約束,在目前名義利率已經降爲零的情況下,隻能單向調控。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沖擊的經驗看,美聯儲都是第一時間采取降息的措施,以快速應對經濟衰退和通縮風險,但政策空間被迅速耗盡。即便将政策利率降爲零,仍可能導緻實際利率過高,也依然不足以扭轉當時市場的悲觀預期。
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在其回憶錄中提及“從2007年8月到2008年1月這6個月内,我們已經把聯邦基金利率從5.25%降低到了3%,比其他幾大央行的反應速度都要快、都要早……我們希望自己看到危機落下帷幕,但最終事實表明,其實危機才剛剛拉開帷幕”。美聯儲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的快速降息也令人記憶猶新。2020年3月3日和3月15日,美聯儲兩次在原定議息會議前緊急降息50BP和100BP,聯邦基金目标利率區間在短短兩周内被迅速調降至0-0.25%。3月15日,在降低貼現窗口利率,并将準備金率降至零的同時,美聯儲不得不推出了7000億美元的量化寬松。當月23日,美聯儲宣布開啓總額不設限的量化寬松,持續買入美債和MBS。
如果考慮零利率約束,泰勒規則也難以在危機時期發揮利率之“錨”的作用。前任美聯儲主席耶倫曾提出,泰勒規則沒有考慮當時貨币政策的特殊性,低估了在當時情景下保持高度寬松貨币政策立場的必要性,因爲與中期充分就業目标相匹配的實際聯邦基金利率均衡值應遠低于曆史平均值,這意味着泰勒規則隐含的利率值明顯過高,制約了經濟複蘇,故難以爲貨币政策決策提供依據。
第二,利率變動将直接影響股市、債市、彙市等金融市場,尤其股市穩定對美國經濟至關重要。早在2020年下半年,标普500指數就突破了前期高點,并不斷創出新高。标普凱斯-席勒全國房價指數漲幅也已超過2008年危機前的高點。去年9月份該指數同比上漲6.96%,創2014年5月以來最大升幅。最新數據顯示,今年7月,标普凱斯-席勒全國房價指數同比上漲19.95%。
事實上,金融穩定在貨币政策決策中的權重日益提升。利率變動往往直接導緻資産價格的重估,這或許是美聯儲對加息頗爲謹慎的一個原因。此外,從金融穩定的角度,需要特别關注尾部風險,即需對可能帶來嚴重經濟後果的小概率事件予以重視。存在尾部風險時,貨币政策需要适當将追求金融安全和流動性放在更高的優先級,而不是固守中長期目标的制約。爲了避免這種尾部風險,往往需要保持比最優水平更加寬松的流動性,在這樣的情況下,數量調控似乎比價格調控更爲适合。
第三,價格型調控将直接影響實體經濟投資,怎樣的利率水平才算适宜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數量型調控的影響則間接得多。融資成本高低是影響實體經濟投資決策的重要因素,如果資本投資回報率還不及融資利率,顯然這樣的投資項目是不應該實施的。價格調控和數量調控最終都影響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但路徑存在差别,前者更爲直接地影響着資金價格信号,後者則通過資金供求逐步形成利率定價。相對而言,數量調控在政策實施中所要面對的市場摩擦更小。一是過剩的流動性将成爲超額存款準備金沉澱下來,不進入信貸市場。二是數量調控不存在爲了尋找一個合适的利率水平而将利率調上、調下,從而擾亂資金價格信号,進而導緻過度投資或投資不足。盡管央行在錨定目标利率時可以參考諸如泰勒規則之類的經驗依據和數據模拟,但這些手段對現實情況的适應性仍然是有限的。
第四,物價對利率上升更加敏感。這是央行對加息持謹慎态度的又一個原因。尤其是多年來通脹持續低迷,達不到美聯儲2%的通脹目标,這事實上拖累了後危機時期貨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在上一輪美聯儲貨币緊縮中,聯邦基金利率最高隻調升至2.5%左右,而曆史上聯邦基金利率中樞基本在5%上下。美國經濟目前仍處于新冠疫情沖擊後的恢複時期,甚至因爲疫情反複而時有波動,爲了防止經濟重新陷入衰退,美聯儲一直都在延遲加息。鮑威爾在傑克遜霍爾年會的發言中解釋道,“貨币政策不應對短期通脹波動作出過度反應……因爲貨币政策對經濟影響的滞後效應甚至可能長達一年以上。目前通脹雖高于2%,但根據平均通脹目标制,長期物價并未超過2%”。從我國的情況看,最近一段時間貨币供應量也不少,但CPI漲幅依然很低,甚至不到1%。
利率調控的上述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當前貨币政策面臨環境發生的變化。首先,爲應對金融動蕩而大幅降低利率後,利率水平恢複到長期均衡水平的步伐緩慢,這壓縮了價格型調控的政策空間,而數量調控更加靈活,理論上不存在上限,且大規模擴表爲數量型調控提供了更多“子彈”,能滿足貨币政策雙向調控的需求。其次,由于經濟金融運行的複雜性,貨币政策操作越來越多地依賴調控者的判斷和經驗,在危機時期尤其如此。而我們在後危機時代面對的新情況、新問題,很多已經大大超出了過往的經驗,需要“摸着石頭過河”。
三、數量調控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央行“有形之手”的不足
數量調控給了央行更多空間觀察經濟運行的變化,其更靈活、可控的特點也有助于彌補央行“有形之手”的不足,幫助中央銀行應對市場摩擦,增加了貨币政策傳導的渠道,也使貨币政策更加靈活适度。
從上一次危機後的經驗看,美國經濟在2013年開始加速恢複,2014年每月新增非農就業平均爲27.5萬人,明顯高于2012年、2013年月均新增19萬的水平,但美聯儲的零利率政策一直持續到2015年底。加息開始前,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2013年6月議息會議後的新聞發布會上首先提出放緩購債步伐、縮減購債規模直至終止購債的計劃。從2014年10月資産購買計劃完全終止到加息前期,經曆了長達一年多的貨币政策觀察期。
而在美聯儲貨币政策正常化的進程中,數量調控也是與價格調控相互配合進行的。美聯儲2017年7月議息會議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在1.00%-1.25%不變,并向市場傳達了即将縮表的信息。由于當時通脹複蘇出現明顯放緩迹象,美聯儲通過先縮表并擱置加息,獲得了更充足的時間觀察經濟表現,以實施适應性的貨币政策。簡而言之,數量調控更适合相機抉擇的需要,尤其是貨币當局面臨複雜局面、需要爲決策判斷留有餘地時,數量調控往往是比較好的方式。
我國貨币政策實踐也得益于數量調控的靈活、可控。我國加入WTO後,人民銀行投放基礎貨币的主要渠道由再貼現和再貸款轉變爲外彙占款。在外彙占款大幅增長階段,人民銀行通過對沖操作部分抵消外彙占款大量增加導緻的基礎貨币擴張。而随着外彙占款收縮,我國貨币供應方式又發生了變化,央行通過創設新的流動性支持工具如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等。“外彙占款” 占央行總資産的比重從高峰時的超過80%,降至目前的56%左右,而“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則從3%左右升至目前的32%左右。
數量調控能同時通過市場預期和資産組合平衡渠道實現貨币政策傳導,這與傳統的價格型調控通過金融機構負債端的傳導相互補充,增加了貨币政策傳導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貨币政策的有效性。貨币政策傳導的信用觀點是央行流動性支持工具創新的一個理論基礎。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伯南克、施蒂格利茨以及托賓等著名經濟學家陸續提出并最終形成了貨币政策傳導的信用觀點。該理論認爲,以貨币爲代表的負債方并不能全面反映貨币政策的傳導過程及其影響,貨币政策還可以通過影響商業銀行信用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的資産方(如債券融資、股票融資等資産方的變動),來影響實體經濟。
具體而言,由于不同類型和期限的資産之間是不完全替代的,危機期間市場對短期資産的流動性和安全性的溢價特别高,并且由于市場功能缺失而使不同資産間的套利交易停滞,資産間可替代性就更差。這就需要美聯儲有針對性地進行資産買賣。此外,美聯儲在以往加息過程中曾經遭遇短端利率上行而長端利率下行的“格林斯潘之謎”。從美聯儲上一輪縮表的經驗看,縮表可以增加長期債券資産供給,從而實現整個收益率曲線的無扭曲上移。再者,數量調控還可以通過影響信貸可得性而使貨币政策傳導更加有效。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貨币政策“二元傳導”機制就是典型的例子,即除了通過金融機構負債端傳導外,還存在信貸渠道的傳導。比如爲了疫情沖擊,我國向疫情防控重點企業提供3000億專項再貸款,并增加了5000億元支農支小再貸款、再貼現額度。而近期我國施行的房地産貸款集中度管理也是一例。
四、财政政策與貨币政策關系轉變與數量調控更相适配
從深層次的原因看,貨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轉變也是銀行倚重數量型調控工具的重要原因,這可能預示中央銀行新調控模式的誕生。以往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更多是相互替代的,當貨币較爲寬松,财政政策往往偏緊或保持穩健,從而使宏觀調控的全局處于一種松緊适度的狀态,很少出現财政政策與貨币政策同時收縮或同時寬松。
而最近一段時間,即使物價漲幅已經突破5%,美聯儲依然保持着寬松的貨币政策;與此同時,拜登政府提出的1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法案已在參議院通過。目前美國國債總額已經高達28.4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130%,但仍在讨論更大規模的支出計劃。現代貨币理論(MMT)的思潮,盡管飽受争議,似乎也反映了這種貨币政策、财政政策雙寬松的現實。該理論認爲,現代貨币體系實際上是一種政府信用貨币體系。它挑戰了财政開支必須量入爲出的傳統經濟學觀念,提出并非先有稅收,再有财政開支,反而是财政開支創造了貨币流通,政府再通過稅收回收貨币。基于該理論,财政赤字并不意味着政府會陷入财政危機,赤字相當于增加貨币供給,因此MMT主張“功能性”财政政策,即财政開支不必量入爲出,而應以促進就業和民生爲原則。
目前,無論是拜登政府還是美聯儲,都“一切以經濟增長爲重”,達成了高度一緻,體現了美國的國家意志。最近十幾年發生的兩次大的危機都使人們重新認識政府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宏觀政策方向的一緻性和穩定性有利于提升國家組織動員能力、資源調配投放能力,爲未來經濟發展開辟更大的空間。顯然數量調控更能适應貨币政策與财政政策關系的這種轉變。
事實表明,在美聯儲大規模資産購買的支持下,美國寬松的财政貨币政策已經深度捆綁。最近一兩年美國國債持有結構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美聯儲大量持有美國國債,其持有美國國債占美國國債總額的比例從2009年末的6.5%上升到2020年末的17%。而根據美聯儲每個星期發布的資産負債表中所持有的美國國債進行計算,截至今年10月20日,美聯儲持有的美國國債占美國國債總額的比例已上升至19.3%,這一數字基本上在以每周0.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增加。從增量看,2020年全年新發美債中,美聯儲持有的比例高達53%。這反映了貨币政策與财政政策的配合。美聯儲通過在二級市場大量購買美國國債,爲美國國債發行創造了有利條件,因爲國債收益率下行會影響新債發行定價,這有助于減輕财政部新發債券的利息負擔。
綜上所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對宏觀金融調控的一次洗禮,時至今日,這次危機的“遺産”仍然影響着世界宏觀經濟運行和國際金融體系,很可能會成爲央行金融宏觀調控的“新常态”。數量調控以其适應複雜決策的靈活性和多樣性、政策力度的可控性和可調節、更加漸進溫和,以及政策效應更容易觀察、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市場摩擦等特點,獲得了中央銀行的青睐。尤其是在人們重新審視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貨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互補的情況下,央行也需要更能适應新形勢的調控手段。
這可能預示着央行新的調控框架的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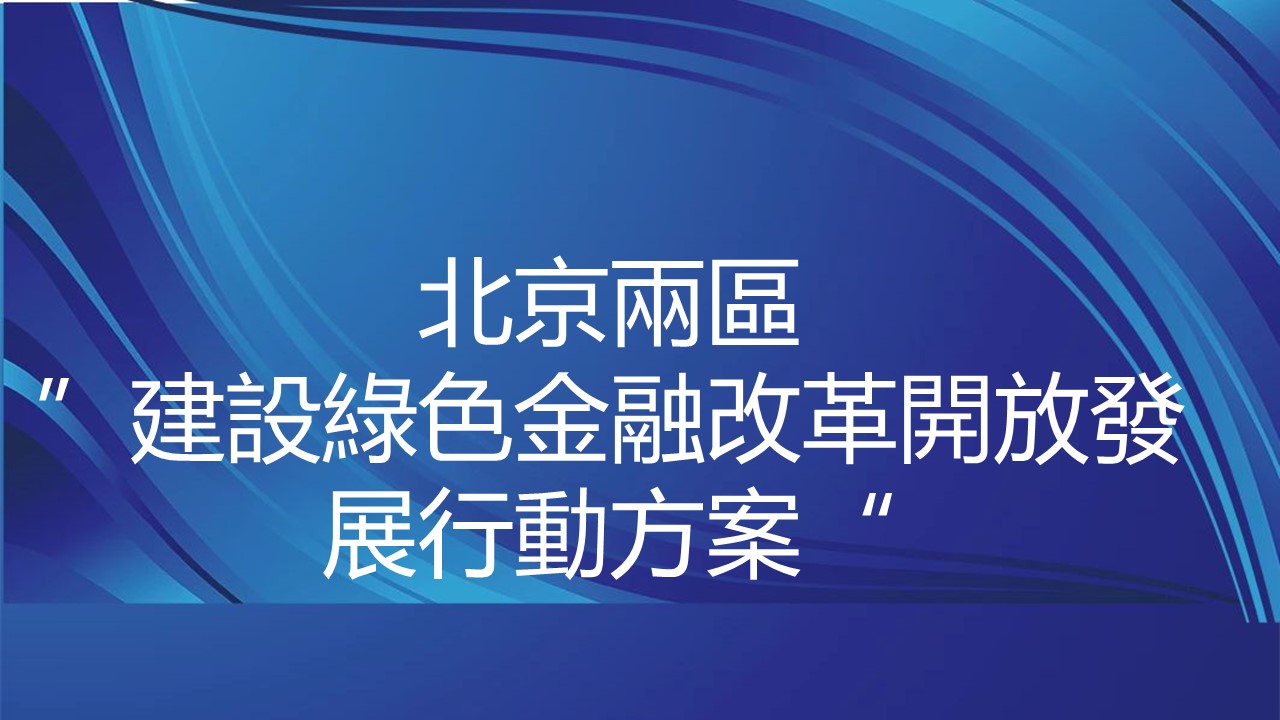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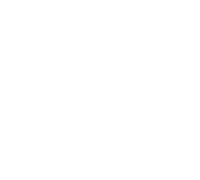




請先 登錄後發表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