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巴別塔的倒塌與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
邵宇 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理事陳達飛 東方證券 宏觀研究員
從英鎊到美元:國際貨幣體系結構變遷
國際貨幣體系是否一定是單極的?單極的貨幣秩序和多極的國際秩序能否相容?近兩百年來的大多數時間裏,確實是以一種貨幣為主導,在強大的網路外部性下,一種貨幣為主的結構符合成本—效率原則。一戰之前是英鎊,二戰之後是美元,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是英鎊向美元過渡階段。英鎊的霸權地位建立在大英帝國強大的海軍和幅員遼闊的海外殖民地基礎之上,英國也因此建立了貿易強國和金融強國地位,倫敦也是當之無愧的國際金融中心。英國以外的國家的主權債務只有在以英鎊計價、在倫敦發行才能享受較低的風險溢價,還需將黃金存放在倫敦的銀行來增加信用。
英國的金融霸權在何時、又是為什麼而轟然倒塌的?
英鎊的信用是建立在與黃金自由地且以穩定比價進行兌換基礎上的。一戰暴發後,為防止黃金外流及其產生的信用收縮,英國於1917年暫停實施金本位,禁止黃金出口與熔煉。暫時退出金本位並不會損害英鎊信用,關鍵是戰後英國能否以戰前平價關係回歸金本位,而英國在這方面保持了優秀的記錄。1925年,英國再次以戰前平價關係回歸金本位。但此時的英國已經不再是昔日的“日不落帝國”。戰前平價高估了英鎊價值(約10%),在國內產生了通縮效應,失業率長期高於10%英國不得不在1931年再次也是永久性地退出了金本位制。頻繁地回歸或退出金本位,削弱了,再加上英國積累的外債和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嚴重削弱了英鎊的信用,也使其隨著英帝國的衰落而式微。
貨幣信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主導貨幣退出的必要條件是存在可替代貨幣,否則全球經貿關係就會陷入“休克狀態”。
在英國和英鎊衰落的同時,美國在崛起,一戰前,美國經濟實力已經全面超越英國。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都有一段時間在“坐山觀虎鬥”。時間差極其寶貴,這使美國在維護金本位的意願和能力方面都超過了英國。一戰時,美國直到1917年參戰後還維持著黃金的可兌換性。雖然美國在1929年遭遇“大蕭條”,但美國直到1933年才退出金本位,比英國晚兩年。從一戰開始到“大蕭條”,美國的黃金儲備在持續增加,經濟基本面也更健康。美元替代英鎊有著充分的理由。截至1929年,美元在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已經達到56%,比英鎊的41%高15個百分點。
二戰後,美國完全確立了金融霸權。1944年建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本質上仍然是金本位制度(金匯兌本位),但在結構上,美元的層級高於一戰之前的英鎊——英鎊的核心地位是建立在更大的規模上,美元的核心地位雖然也表現為更大的規模,但這又是作為更高層級的結果而出現的,美元取得了與黃金直接綁定的唯一資格(見圖1)。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所以是一種雙層嵌套式的貨幣體系,有種“挾黃金以令諸侯”的意思。美元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黃金的貨幣屬性。
圖1 國際貨幣體系結構的變遷來源:筆者繪製,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
1973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在後佈雷頓森林體系中,黃金的儲備貨幣地位變成了一種象徵,貨幣屬性盡失,不再發揮交易媒介和價值尺度職能,美元成了唯一的“錨貨幣”。雖然歐元、英鎊、日元和人民幣也被認為是國際貨幣,但相對於美元來說,仍處於“週邊”。在後佈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元的地位等價於金本位時代的黃金。
尼克森關閉黃金窗口,是一次實質性的違約。在初期,美元秩序的重建與“石油美元”有很大關系,而現在則主要建立在美國國債和美國政府的信用之上——如徵稅能力,也就是Zoltan所說的內部貨幣——國債既是美元信用的基礎,也是美聯儲創造基礎貨幣的媒介。由此,美聯儲才能較好地承擔“最後貸款人”職能,也能在市場遭受流動性衝擊時發揮“最後交易商”職能。
除了網路外部性和美聯儲的誕生等原因,從結構上講,美元之所以能夠較快地取代英鎊而成為最重要的世界貨幣,是因為在金本位體系中,英鎊的公信力不僅受到財政紀律的約束,還受到黃金儲備的限制,黃金對英鎊有更高一層的替代性。正是因為黃金的這種替代作用,再加上戰爭期間英國黃金儲備的流失和美國黃金儲備的增加,才加速了美元對英鎊的替代。但在當前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並不存在這樣一個超主權的第三方貨幣對美元形成替代,從而也增加了美元的“鎖定效應”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難度。換言之,貨幣的網路外部性在純信用貨幣時代比在金本位時代更為強大。
不可置否,美元的信用正在受到質疑。在純信用的美元體系下,美債理論上不存在可兌付的問題,但持續的貶值是隱性的違約。在通脹壓力倍增的當下,不斷擴大的財政赤字的可持續性存在疑問(見圖2)。與佈雷頓森林體系一樣,後佈雷頓森林體系仍未解決“特裏芬難題”,持續並不斷擴大的國際收支逆差是滿足美元需求的必要,但同時也在侵蝕美元的信用。通貨膨脹、負利率或美元貶值,都是對這一扭曲結構必要的校正。
圖2 美國的雙赤字在資金流量表上的映射(截至2021年9月)
數據來源:美聯儲,CEIC,東方證券財富研究中心
數據說明:國外部門的資本淨流入對應著經常帳戶的逆差。
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金融強國與人民幣安全資產
未來的貨幣秩序,還是單極嗎?如果我們傾向於認為世界秩序是多極的——三足鼎立,美洲以美國為中心,歐洲以德國為中心,亞洲以中國為中心。那麼貨幣大概率也會是多極的,只是未見得在份額上完全匹配。
筆者對人民幣借由“商品貨幣”的概念取代美元而成為“佈雷頓森林Ⅲ”體系的核心貨幣的構想持謹慎樂觀態度。俄烏衝突確實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戰略機遇期,但“石油美元”的故事較難重演。
拋開戰爭本身的不確定性,其一,金塊已毫無貨幣屬性可言;其二,全球碳中和背景下,21世紀“石油人民幣”的地位已難等同於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美元”,俄烏衝突會加速全球的能源轉型,石油的戰略地位也會隨之下降;其三,人民幣國際化更需建立在金融強國而不是局限於貿易大國上。這方面任重道遠,相比國內資本市場的基礎性制度建設而言,增強匯率彈性和解除資本管制的難度只能排在次要的位置上(艾肯格林,《全球失衡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教訓》,第四章)。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雖成效顯著,但與紐約、倫敦等仍有距離。更重要的是,我國尚缺乏對國際投資者有吸引力的金融安全資產。
如果將2008年金融危機視為舊的全球化體系的崩潰,那目前就處在重構的過程中。趨於新均衡的過程就是利益再分配的過程,衝突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貿易戰和貨幣戰均是分配的手段。中國突圍的關鍵,是建立國家金融能力,人民幣國際化扮演著重要角色,其國際化的水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民幣所體現出來的公共品屬性:消費者是否需要人民幣來購買中國的製成品;生產者是否需要人民幣來購買中國的中間品或技術;投資者是否需要人民幣來存儲價值,或實現價值增值。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人民幣國際化主要體現在第一個層次,這是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外溢。實踐證明,僅靠貿易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阻力較大,空間有限。所以,未來或應加強人民幣在後兩者的體現,這分別要求中國提升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和建設健全、開放的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前者主要依託於基礎性科技創新能力和品牌能力,後者則依託於法律、監管等制度建設,逐漸消除金融抑制帶來的交易成本。這兩個方面,並非是獨立的,因為研究表明,相較於銀行信貸融資而言,權益類融資更有助於促進創新。
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的必然性邏輯是建立在傳統的以投資驅動和出口拉動為主體,以金融抑制為條件可以壓低資本成本和強制儲蓄的模式之上的。這種模式有助於中國在資本要素短缺的情況下快速實現工業化,但當中也積累了大量的扭曲。隨著GDP總量和人均GDP增速的提高,以及中國經濟發展方略從高速度向高質量發展的轉換,金融抑制性政策對GDP的貢獻已經由正轉負,GDP的進一步提高要求供給側動能由廉價要素投入轉變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和創新驅動,這就要求與之相匹配的金融市場配置效率。
我們認為,中國金融改革的方向是確定的,一方面,就是消除金融抑制,即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政府逐步退出信貸的分配、逐步放鬆資本帳戶管制,以及加大銀行等金融服務業的開放等;另一方面,就是要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功能。這是金融供給側改革確定性的方向,也是提升中國在全球範圍內提供金融公共品能力的必然要求。
全球化總是在重複著失衡與重構、脫鉤與突圍的故事,只是角色在不斷變化,然而,至少從歷史經驗看,不變的是全球化似乎在沿著既定的方向不斷前進。21世紀並不必然是亞洲或者中國的世紀,中國主導的全球化秩序也不必然超過美國,這一切,都取決於相對意義上的國家能力,它集中體現為提供公共品的能力。
《聖經·舊約》中,人類為了上天堂,建造了一座塔,被稱為“巴別塔”。為了阻止人類的瘋狂,上帝使人類說不通的語言,叫其不能溝通,計畫隨之破裂。“巴別塔”常被用來比喻權力的單極結構或等級關係(弗格森用參考弗格森,《廣場與高塔》)。美國被認為是最後的全球霸權國家,隨著世界秩序的多極化,貨幣巴別塔是否會隨之倒塌?重建後的世界,是另一座塔還是三座塔?非主權的數字貨幣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巴蒂亞,《貨幣金字塔》)?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石油人民幣與數字人民幣各扮演著什麼角色?
內容來源:復旦金融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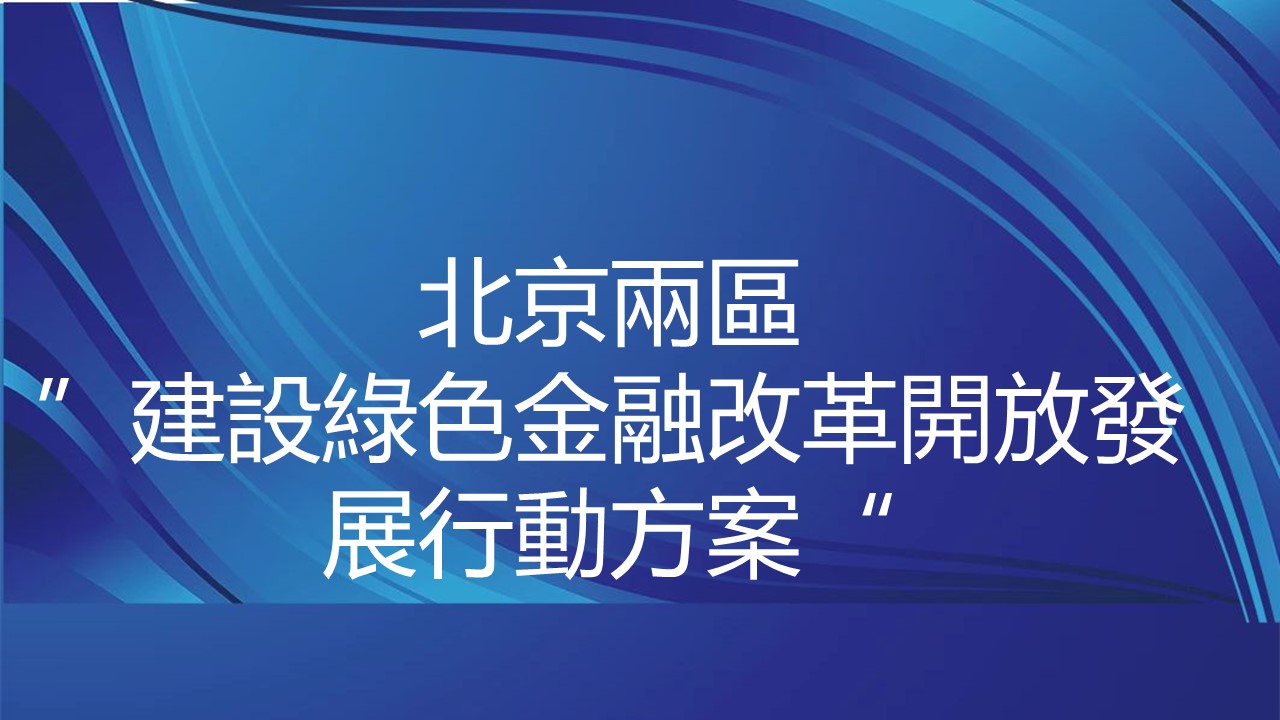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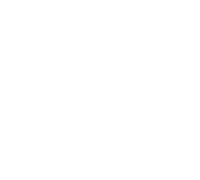




請先 登錄後發表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