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币”发展新思路:與SDR挂钩成为超主权货币
如何理解貨幣作為監管媒介的功能?不妨從“長臂管轄”講起。這原是美國民事訴訟的概念,指地方法院將管轄權延伸至州外乃至國外的被告。例如,最近有過百間在美上市的中概股被美國證監會放入擬除牌和確定除牌名單,因企業處於大中華區的會計師事務所無法向美方提供審計底稿。這種跨境審計便是採用“長臂管轄”原則——就算企業的實際運作不在美國,只要產品在美國交易、以美元定價,就要接受美國法院的管轄。
按照肖耿的說法,港幣也可以作為一種“監管媒介”,所有以港元定價的交易,都歸入香港的監管體系當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貨幣作為監管媒介實際上是‘根深蒂固’的,除了政治和法律基礎之外,就是貨幣了。”肖耿指出,“《基本法》裡保護港幣的地位,最重要就是確立港幣的監管功能。”
進一步說,港幣監管體系之所以具備認受性,離不開普通法系(Common Law)的法治根基,更離不開特區政府在制度基建上長年累月的投入。五年前,適逢香港回歸20周年,彼時還在香港大學任教職的肖耿在《中國金融雜誌》刊發文章《香港緣何成為金融中心》,當中提到若要把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核心競爭力總結為一條,便是“市場交易的邊際制度成本很低”。
文章解釋,香港在維護自由市場基礎設施上投資巨大,有著高昂的固定成本。例如,香港公務員、監管部門的專業人士、員警及社會機構雇員的薪酬水準與市場看齊,人數也相當多。另一方面,香港經濟效率高、稅率極低、財務狀況健康、政府沒有內外債,能夠支持這一固定成本開支。“高昂的固定制度成本得到的回報是極低的邊際市場交易成本,也就是市場交易量增加時,每單位交易量平攤的制度成本非常低。”肖耿寫道。
因此,縱使香港的土地、人力等生產要素價格高昂,其極低的邊際制度成本與國際接軌的監管體系,仍能成功吸引並留住大批國際企業,成就國際金融中心的美譽。
02
與SDR掛鉤成為超主權貨幣
肖耿憶述在課堂上提問學生,什麼是“Made in Hong Kong”(香港製造),惟學生僅能答出一些特色菜式。“真正‘Made in Hong Kong’的就是‘Hong Kong Dollar’,港幣才是真正的香港品牌。”
對於“香港特色”,從“貨幣作為監管媒介”的理論角度出發,很多陳詞濫調都會有新變化。例如過去被奉若圭臬的“港元—美元聯繫匯率制度”。肖耿指出,香港過去對“貨幣制度”理解過於簡單,一味強調港元與美元掛鉤,“好像覺得那是最重要的”。
“但並不是的,港幣跟美元掛鉤只是一個‘貨幣定價’的問題,意味著它的貨幣政策必須緊跟美國的貨幣政策。”肖耿釐清邏輯道,“聯繫匯率的貨幣制度,意味著香港監管體系是有獨立性的,是能得到全球認可的。在此基礎上,聯繫匯率是跟英鎊掛鈎,還是跟歐元掛鈎,還是美元或人民幣掛鈎,這都是次要的。”
早在二十年前,肖耿就提出,港幣可以踏出“破天荒”的一步,考慮匯率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SDR)掛鉤。SDR由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貨幣組成,按照各國的國際貿易及金融體量劃分比例。據IMF在今年五月的調整,SDR貨幣籃子最近新比例為美元權重43.38%,歐元權重29.31%,人民幣權重12.28%,日圓權重7.59%,英鎊7.44%。
“到目前為止,我依然認為這是最公平、最實際,也是對全球最好的國際貨幣體系。”肖耿表示,由IMF這類多邊組織去推動的可能性較小,但從市場推動可能性很大,“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香港主動去擁抱全球化,擁抱和平、多贏的格局。”
肖耿指,若港幣與SDR掛鉤,就會成為超主權的國際貨幣,而香港金融資產也可成為SDR流動性資產的一部分。這對許多不想依附大國的小型經濟體,例如新加坡、杜拜,十分有吸引力。
03
極端下掛鉤人民幣打破瓶頸
時易境遷,地緣政治日趨緊張,肖耿也更新觀點,認為“港幣在極端情況下可掛鉤人民幣”,而這將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化打破瓶頸。
肖耿指出,人民幣國際化有兩條路徑,一是離岸市場的建設,二是在岸市場的開放。離岸方面,雖然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當局都有推出一些相應的離岸人民幣產品,但是依然未成體系,較為碎片化;在岸方面,中國雖已形成較為完整的在岸金融體系,但仍有資本帳戶管制,“考慮到國際形勢,人民幣在岸市場不可能完全、徹底地開放”,而這也是導致離岸人民幣產品碎片化的原因之一。
離岸人民幣市場因而缺乏風險管理的功能。“比較一下港幣體系就很明顯了。”肖耿分析,港幣市場有股票、債券、外匯市場、房地產、風險投資,“在香港持有的財富,會放一部分在股票,一部分在房地產,一部分債券,可以通過投資組合進行風險管理。”
相較之下,離岸人民幣產品都是過渡的(transitory)資產形式。“要麼就轉成在岸人民幣回流,要麼就換成港幣、美元或者歐元等其他貨幣,就變成了海外資產。”這也導致離岸人民幣的發展呈現出隨著升貶值而流出流入的歷史特徵。
若想破除人民幣國際化這一難點,最順理成章的做法,便是讓港幣與離岸人民幣掛鉤,“離岸人民幣也有了完整的金融體系和風險管理的可能性”。
“每一個選擇都有利弊。”肖耿表明,他只是為香港未來提供選擇,“不是現在就要改。”他續指,若港幣與其他貨幣掛鉤,也會失去與美元掛鉤的好處,例如認受性高,國際交易結算簡單;而與美元掛鉤也有壞處,例如貨幣政策要完全跟隨美國,無法完全顧及本地經濟。
“即使香港跟美元,跟SWIFT一點關係都沒有,香港依然可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肖耿解釋,美國制裁只能制裁香港所持有的美元儲備,對香港的監管體系、資本市場根本沒有約束力,“香港是個開放經濟體,歡迎全世界的買家和賣家來香港進行交易。”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香港對國家的作用非常重要,因為它是外迴圈裡成熟的制度體系。”肖耿在評論文章中稱,香港的貨幣與商業體系具有國際競爭力、親和力,是國家軟實力的核心資產,“需要充分用好,保護好”。
04
以灣區腹地打造“特區中特區”
誠然,作為發達經濟體,香港擁有內地城市無法比擬的制度優勢。“香港作為一個與西方發達社會高度相容的世界城市,有許多‘最後一公里’的制度與實踐細節非常值得內地學習借鑒。”上述肖耿所撰《香港緣何成為金融中心》如是寫到,又以廉政公署、財產保護及糾紛解決機制、簡單稅制為例證。
然而,肖耿不止看到香港的優勢,也看到香港的劣勢:“香港的親和力能用來吸引全世界的企業和人來高效工作和舒服生活,但香港現在只有一半的條件。”
何謂“一半的條件”?“香港制度是很好的,但是物理空間不足。”肖耿解釋,大城市群發展具有梯度,若中心城市的生產成本的提高,會驅使實體產業或中低收入人群離開前往周邊城市,便形成“腹地”。“曼哈頓是中心,離它愈遠,樓價就會愈便宜。產業同樣也會根據樓價進行分佈。”肖耿舉例,要設工廠、建荷裡活,沒必要放在曼哈頓,但是設投資銀行、律師事務所就會在曼哈頓。
肖耿比喻,香港是“失去腹地的曼哈頓”。本地金融業的蓬勃帶動了房地產、會計、法律等一系列行業,也把人力、土地等生產成本提高,“反而導致產業的空洞化”。同時,“一國兩制”之下,港人不願離開香港,因為離開香港意味著“失去香港的制度環境”。於是,即便香港坐擁制度優勢,也受限於物理空間,產業結構畸形。因此,肖耿指出,香港需要“擴容”以提升制度的供給能力。
因此,肖耿提出“特區中的特區”方案,在香港周邊的試驗區,如橫琴、前海、南沙,把香港的制度以“氣泡”形式、以市場主體為單位嵌入試驗區。例如,在試驗區內引入香港的銀行、醫院、學校甚至社服機構,聘請港籍人士,以香港的監管、制度來運作,提供境外離岸服務,“這不就等於擴大了香港嗎?”
同樣地,肖耿建議香港可以嘗試在北部都會區引入內地制度,參考“一二線”形式。例如,設計一個有“一線”和“二線”的管制區:一線的管制可以相對寬鬆,內地人要去買免稅商品、享受一些香港的服務,可以當天來回;“二線”可引進內地市場主體在香港的轄區內按內地的監管體系運行。肖耿提到,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期間,特區政府通過《緊急法》引進內地工程隊、醫療隊在河套地區修建方艙醫院,便是實踐“一二線”的概念,“其實就是加建一條橋,然後讓內地隊伍過去修建,然後圍封起來。
”
肖耿表示,精准監管的“制度氣泡”在過去是不能想像的,“但是在現在的數位化環境,我認為是完全有可能的。”肖耿憶述自己在香港證監會的工作,表示“監管”本質上都是監管機構向企業索取資料以掌握動向。在資料已經“數位化”的今天,通過技術實現遙距跨區監管絕非“天馬行空”,不必再拘泥於“屬地原則”的傳統監管。
肖耿强调,制度合作并非“合并”,两地都需保留自己的制度特色,才能双赢:“香港的体制是‘海水’,内地的体制是‘河水’,海水和河水不能搞混。香港的机构是‘海虾’,内地机构是‘河虾’,两者都不能适应彼此的环境,所以不能搞混,但可以互相渗透和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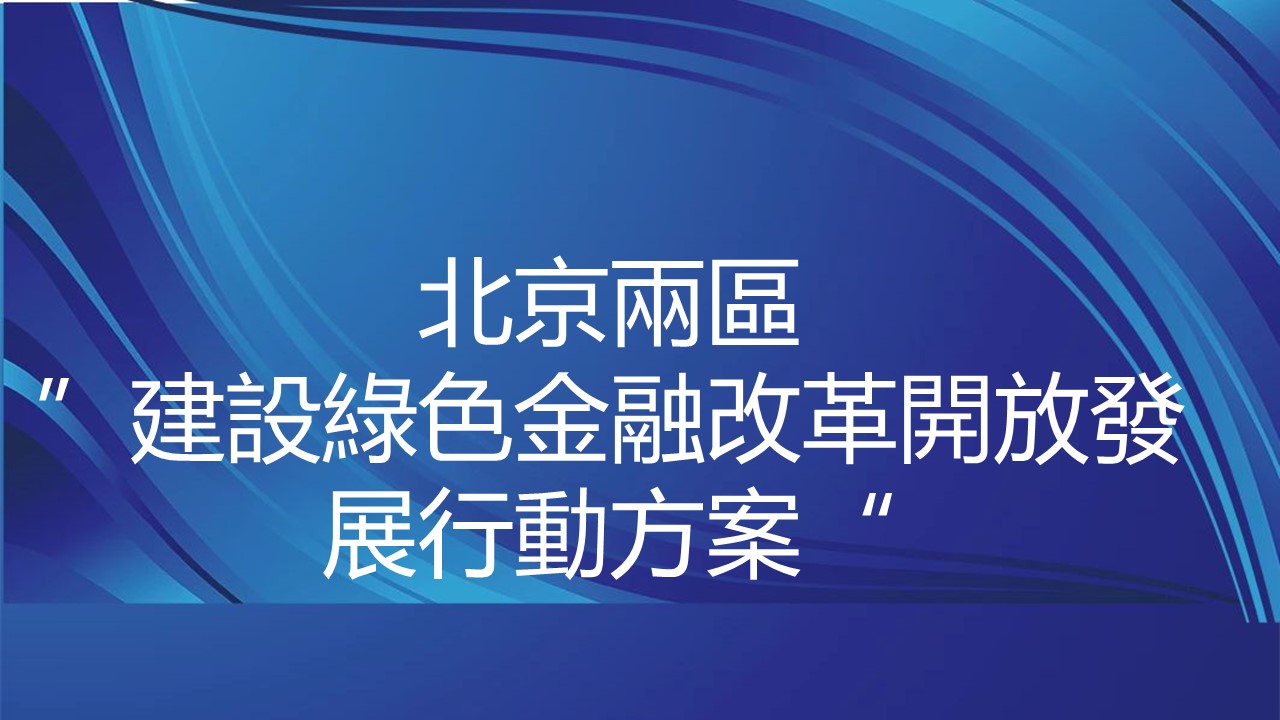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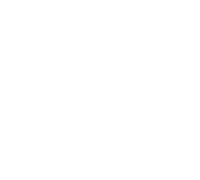




請先 登錄後發表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