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币”发展新思路:与SDR挂钩成为超主权货币
如何理解货币作为监管媒介的功能?不妨从“长臂管辖”讲起。这原是美国民事诉讼的概念,指地方法院将管辖权延伸至州外乃至国外的被告。例如,最近有过百间在美上市的中概股被美国证监会放入拟除牌和确定除牌名单,因企业处于大中华区的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向美方提供审计底稿。这种跨境审计便是采用“长臂管辖”原则——就算企业的实际运作不在美国,只要产品在美国交易、以美元定价,就要接受美国法院的管辖。
按照肖耿的说法,港币也可以作为一种“监管媒介”,所有以港元定价的交易,都归入香港的监管体系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货币作为监管媒介实际上是‘根深蒂固’的,除了政治和法律基础之外,就是货币了。”肖耿指出,“《基本法》里保护港币的地位,最重要就是确立港币的监管功能。”
进一步说,港币监管体系之所以具备认受性,离不开普通法系(Common Law)的法治根基,更离不开特区政府在制度基建上长年累月的投入。五年前,适逢香港回归20周年,彼时还在香港大学任教职的肖耿在《中国金融杂志》刊发文章《香港缘何成为金融中心》,当中提到若要把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核心竞争力总结为一条,便是“市场交易的边际制度成本很低”。
文章解释,香港在维护自由市场基础设施上投资巨大,有着高昂的固定成本。例如,香港公务员、监管部门的专业人士、警察及社会机构雇员的薪酬水平与市场看齐,人数也相当多。另一方面,香港经济效率高、税率极低、财务状况健康、政府没有内外债,能够支持这一固定成本开支。“高昂的固定制度成本得到的回报是极低的边际市场交易成本,也就是市场交易量增加时,每单位交易量平摊的制度成本非常低。”肖耿写道。
因此,纵使香港的土地、人力等生产要素价格高昂,其极低的边际制度成本与国际接轨的监管体系,仍能成功吸引并留住大批国际企业,成就国际金融中心的美誉。
02
与SDR挂钩成为超主权货币
肖耿忆述在课堂上提问学生,什么是“Made in Hong Kong”(香港制造),惟学生仅能答出一些特色菜式。“真正‘Made in Hong Kong’的就是‘Hong Kong Dollar’,港币才是真正的香港品牌。”
对于“香港特色”,从“货币作为监管媒介”的理论角度出发,很多陈词滥调都会有新变化。例如过去被奉若圭臬的“港元—美元联系汇率制度”。肖耿指出,香港过去对“货币制度”理解过于简单,一味强调港元与美元挂钩,“好像觉得那是最重要的”。
“但并不是的,港币跟美元挂钩只是一个‘货币定价’的问题,意味着它的货币政策必须紧跟美国的货币政策。”肖耿釐清逻辑道,“联系汇率的货币制度,意味着香港监管体系是有独立性的,是能得到全球认可的。在此基础上,联繫汇率是跟英镑挂鈎,还是跟欧元挂鈎,还是美元或人民币挂鈎,这都是次要的。”
早在二十年前,肖耿就提出,港币可以踏出“破天荒”的一步,考虑汇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挂钩。SDR由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组成,按照各国的国际贸易及金融体量划分比例。据IMF在今年五月的调整,SDR货币篮子最近新比例为美元权重43.38%,欧元权重29.31%,人民币权重12.28%,日圆权重7.59%,英镑7.44%。
“到目前为止,我依然认为这是最公平、最实际,也是对全球最好的国际货币体系。”肖耿表示,由IMF这类多边组织去推动的可能性较小,但从市场推动可能性很大,“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香港主动去拥抱全球化,拥抱和平、多赢的格局。”
肖耿指,若港币与SDR挂钩,就会成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而香港金融资产也可成为SDR流动性资产的一部分。这对许多不想依附大国的小型经济体,例如新加坡、杜拜,十分有吸引力。
03
极端下挂钩人民币打破瓶颈
时易境迁,地缘政治日趋紧张,肖耿也更新观点,认为“港币在极端情况下可挂钩人民币”,而这将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打破瓶颈。
肖耿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有两条路径,一是离岸市场的建设,二是在岸市场的开放。离岸方面,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当局都有推出一些相应的离岸人民币产品,但是依然未成体系,较为碎片化;在岸方面,中国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在岸金融体系,但仍有资本账户管制,“考虑到国际形势,人民币在岸市场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开放”,而这也是导致离岸人民币产品碎片化的原因之一。
离岸人民币市场因而缺乏风险管理的功能。“比较一下港币体系就很明显了。”肖耿分析,港币市场有股票、债券、外汇市场、房地产、风险投资,“在香港持有的财富,会放一部分在股票,一部分在房地产,一部分债券,可以通过投资组合进行风险管理。”
相较之下,离岸人民币产品都是过渡的(transitory)资产形式。“要么就转成在岸人民币回流,要么就换成港币、美元或者欧元等其他货币,就变成了海外资产。”这也导致离岸人民币的发展呈现出随着升贬值而流出流入的历史特征。
若想破除人民币国际化这一难点,最顺理成章的做法,便是让港币与离岸人民币挂钩,“离岸人民币也有了完整的金融体系和风险管理的可能性”。
“每一个选择都有利弊。”肖耿表明,他只是为香港未来提供选择,“不是现在就要改。”他续指,若港币与其他货币挂钩,也会失去与美元挂钩的好处,例如认受性高,国际交易结算简单;而与美元挂钩也有坏处,例如货币政策要完全跟随美国,无法完全顾及本地经济。
“即使香港跟美元,跟SWIFT一点关系都没有,香港依然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肖耿解释,美国制裁只能制裁香港所持有的美元储备,对香港的监管体系、资本市场根本没有约束力,“香港是个开放经济体,欢迎全世界的买家和卖家来香港进行交易。”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香港对国家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外循环里成熟的制度体系。”肖耿在评论文章中称,香港的货币与商业体系具有国际竞争力、亲和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资产,“需要充分用好,保护好”。
04
以湾区腹地打造“特区中特区”
诚然,作为发达经济体,香港拥有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制度优势。“香港作为一个与西方发达社会高度相容的世界城市,有许多‘最后一公里’的制度与实践细节非常值得内地学习借鉴。”上述肖耿所撰《香港缘何成为金融中心》如是写到,又以廉政公署、财产保护及纠纷解决机制、简单税制为例证。
然而,肖耿不止看到香港的优势,也看到香港的劣势:“香港的亲和力能用来吸引全世界的企业和人来高效工作和舒服生活,但香港现在只有一半的条件。”
何谓“一半的条件”?“香港制度是很好的,但是物理空间不足。”肖耿解释,大城市群发展具有梯度,若中心城市的生产成本的提高,会驱使实体产业或中低收入人群离开前往周边城市,便形成“腹地”。“曼哈顿是中心,离它愈远,楼价就会愈便宜。产业同样也会根据楼价进行分布。”肖耿举例,要设工厂、建荷里活,没必要放在曼哈顿,但是设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就会在曼哈顿。
肖耿比喻,香港是“失去腹地的曼哈顿”。本地金融业的蓬勃带动了房地产、会计、法律等一系列行业,也把人力、土地等生产成本提高,“反而导致产业的空洞化”。同时,“一国两制”之下,港人不愿离开香港,因为离开香港意味着“失去香港的制度环境”。于是,即便香港坐拥制度优势,也受限于物理空间,产业结构畸形。因此,肖耿指出,香港需要“扩容”以提升制度的供给能力。
因此,肖耿提出“特区中的特区”方案,在香港周边的试验区,如横琴、前海、南沙,把香港的制度以“气泡”形式、以市场主体为单位嵌入试验区。例如,在试验区内引入香港的银行、医院、学校甚至社服机构,聘请港籍人士,以香港的监管、制度来运作,提供境外离岸服务,“这不就等于扩大了香港吗?”
同样地,肖耿建议香港可以尝试在北部都会区引入内地制度,参考“一二线”形式。例如,设计一个有“一线”和“二线”的管制区:一线的管制可以相对宽松,内地人要去买免税商品、享受一些香港的服务,可以当天来回;“二线”可引进内地市场主体在香港的辖区内按内地的监管体系运行。肖耿提到,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特区政府通过《紧急法》引进内地工程队、医疗队在河套地区修建方舱医院,便是实践“一二线”的概念,“其实就是加建一条桥,然后让内地队伍过去修建,然后围封起来。”
肖耿表示,精准监管的“制度气泡”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但是在现在的数字化环境,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的。”肖耿忆述自己在香港证监会的工作,表示“监管”本质上都是监管机构向企业索取数据以掌握动向。在数据已经“数字化”的今天,通过技术实现遥距跨区监管绝非“天马行空”,不必再拘泥于“属地原则”的传统监管。
肖耿强调,制度合作并非“合并”,两地都需保留自己的制度特色,才能双赢:“香港的体制是‘海水’,内地的体制是‘河水’,海水和河水不能搞混。香港的机构是‘海虾’,内地机构是‘河虾’,两者都不能适应彼此的环境,所以不能搞混,但可以互相渗透和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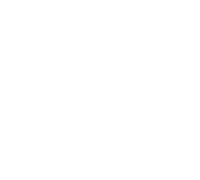




请先 登录后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