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3年本科生课程《国际组织与国际法》案例分析习作。
作者文责自负,敬请批评指正。引言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以下除他人著作或文件可能称“亚行”、引用时照录原状外,一律简称亚开行)是在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支持下建立的区域性开发金融银行。不管是历史过程还是逻辑序列上,亚开行都是亚洲金融秩序建立中重要的中间环节,处在世界银行这样的全球性开发金融银行和亚投行这一专门性极强的区域开发金融银行之间。本文从创立过程与机构宗旨、议题领域与成员构成、组织结构、决策制度等角度对亚开行展开研究,致力于通过制度分析和比较,揭示亚开行的区域与时代性质,并希望能稍稍揭示国际开发金融组织的发展逻辑,探讨亚投行与亚开行的关系问题。
本文第一部分从宏观上关注亚开行的目标与定位,及其在历史维度上的演变,分析亚开行宗旨的设定和在此基础上业务范围的改变。第二部分具体分析其种种制度设计,包括股权和投票权的分配、理事会和执董会的设置以及相关的名额分配问题,以及行长的选择。第三部分关注亚开行创设过程中的博弈与运作时的现实政治因素,试图揭示亚开行的现实性所带来的局限,以及亚投行在这方面的相对优势。一、宗旨与业务范围
1966年11月24日,亚洲开发银行成立,总部设在菲律宾马尼拉,此时有31个成员,日本人渡边武出任首任行长(麦考利,2020:1-2)。在此前的1965年10月,筹备委员会拟定了《亚行章程》,其中规定亚开行的宗旨是“促进亚洲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合作,并协助本地区的发展中成员集体和单独地加速经济发展的进程”(ADB,1966:2)。同时规定亚开行有如下职能(function):促进本地区以开发为目的的公私资本的投资;为发展中成员提供资金,优先考虑有利于“整个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以及“较小或较不发达的成员的”工程项目和计划;为发展类项目和计划提供技术援助;同联合国及其他相关组织展开合作(ADB,1966:2)。 亚开行最初十年的工作即以此为纲领展开。截至1976年底,亚开行向23个国家提供各种借贷款30多亿美元,其中25%以上以优惠贷款的形式提供给最贫困的成员;业务批准总额的23%投入能源领域,20%投资交通和通讯技术项目,19%投资农业项目,18%投资金融项目,10%投入工业项目,9%投入水利工程,1%左右投入教育(麦考利,2020:87-88)。其中,农业项目相对更多地使用亚洲开发基金贷款(占全部开发基金贷款的34%)。另外,技术援助十年间达到2540万美元。
此后,如果以每十年为一个节点,我们可以从贷款数额和项目领域的变动消长勾勒出亚行自身定位与业务范围的流变。1977-1986这十年间,在行长吉田太郎一等人的推动下,粮食供应、出口、就业成为重要议题,亚行贷款业务向农业和能源领域有意倾斜,业务批准总额160亿美元中农业项目占31%,成为最大板块,能源项目则占据25%(麦考利,2020:127-128);为应对石油危机及其后果,在改革之后,金融项目和技术援助的额度也大幅提升,前者占业务批准总额的10%,后者达到1.25亿美元,是上一个十年的五倍(麦考利,2020:128)。而从1987年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农业领域的占比明显下降了,三个十年里分别为16%、9%和6%,实际金额则稳定在5000到8000百万美元之间;这是因为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借款国对贷款领域有所偏好和选择(麦考利,2020:203、250、308)。金融项目的占比在第四个十年即1997-2006年间达到惊人的23%(第三个和第五个十年分别占11%和12%),则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麦考利,2020:249-250)。 可以看出,围绕既定宗旨,亚开行的实际政策以及政策指导下的款项流向是非常灵活且适应现实的。或许正如其首任行长渡边武所说,亚开行是亚太地区的“家庭医生”;如果说最初十年的灵活和谨慎是出于对新建立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定位和职能的探索与尝试,那么此后一以贯之的应变性和问题导向性则是对其建立时的初衷“简洁高效”、“解决问题”原则的秉持。 这一特质使得亚开行在建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时刻关注时代议题,站在亚太地区发展的重要节点,是其一直保持活力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也会导致随着时间推移,亚开行的工作情况与其最初建立时产生比较大的迁移变化。 尤其应当关注“技术援助”板块的变化。第一个十年的技术援助金额仅为各类业务批准总额的0.847%;第二个十年开始,亚开行“对借款国的政策问题和机构发展越来越感兴趣”,这个十年的技术援助达到1.25亿美元(麦考利,2020:177),也是在此期间亚开行的知识和信息数据库开始建设,并开始定期刊布区域经济发展趋势调查和主要经济领域报告(麦考利,2020:5);到第三个十年,技术援助金额8.82亿美元,已经达到业务批准金额(430亿美元)的2%,这一数字在第四和第五个十年里分别达到14亿和15亿美元,其中第四个十年间的技术援助金额能够达到业务批准总额的2.2%(麦考利,2020:251、307)。从这个切面,我们可以看出亚开行的业务重心、援助方式乃至援助理念,都在时代中产生了巨大的流变。当然,这受到亚开行本身资金与能力、经验方面的一些限制,详见后文;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一变化与当时世界上或许最重要的多边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旨趣与业务重心的改变也应当是平行的。二、制度设计:全球性与区域性的平衡
从“东京研究小组”的组建算起的话,亚洲开发银行的筹建开始于1963年,最终成立于1966年底,那时区域性的多边开发银行只有欧洲投资银行、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屈指可数的几家,而全球性多边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成立也才20年左右。在可资借鉴的案例相对缺乏的时候,如何从制度上定位和设计一家亚洲的区域开发银行成为当时的筹建者必须审慎考虑的问题。
成员构成与股权分配方面的设计或许最直观地凸显其区域特性。在1965年拟定的《亚行章程》里,保持“亚行的亚洲特征”被视为重要原则,因此对亚洲非联合国成员和非亚洲成员的接纳经历了一场辩论(麦考利,2020:39)。最终商定允许非亚洲成员加入后,《章程》必然地对其持股总数有一限制;最终这一数字商定为亚洲成员持股总数不低于股本总额的60%(ADB,1966:4)。对比美洲开发银行直接从表决权层面规定域内国家总表决权不得低于50%,亚开行的设计应该说是更精确和易于管理的,也杜绝了表决权计算中可能存在的复杂情况和“操作空间”。
图二:ADB的组织结构
来源:https://www.adb.org/what-we-do
亚开行的主要机构是理事会和董事会,另有一批局、处和办公室,设置在由行长负责的总部之下(《亚洲开发银行》,1987:15)。理事会作为全体机构,每个成员体派出一正一副两名理事,每年定期举行会议,掌握机构的一切决策权;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ADB,1966:21-22)。董事会负责行使章程规定、理事会授予的部分职权;董事在划定的若干选区内产生,1966年有10个选区、产生10名董事,其中7名来自域内成员体,3名来自域外成员体;1971年开始,变为12个选区产生12名董事,其中8名来自域内,4名来自域外(麦考利,2020:375)。理事会选举产生的行长(行长缺席时由副行长代替,副行长由行长向董事会举荐产生)担任董事会主席,是最高行政负责人,依需要或请求召开董事会会议(ADB,1966:24)。总部是亚开行的行政机构,1966年底仅有40名员工,到2022年底扩张到3767名。另外,还有若干专业和专门性质的局和办公室等,此处不赘。
投票权的分配与集中机制决定了机构的权力结构。每位理事在亚开行理事会的投票权是基础票和股权票加和而成的。截至2022年底,域内成员体的持股占总额的63.390%,而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65.124%;其中投票权最高的成员体是日本(域内)和美国(域外),均为12.751%,其次是中国(域内,5.437%)。可以看出,亚开行通过基础票的设计,使域内国家,尤其是欠发达的小国,在理事会相对拥有了较高的投票权;这是其“坚持区域特征”的纲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的反映。至于投票权集中原则,在亚开行表现为多数制,《章程》规定除了特殊事项之外一般遵循简单多数制(ADB,1966:21)。实际上学者们指出,理事会对事项的通过需要的票数一般应达到总票数的三分之二(《亚洲开发银行》,1987:17-18)。 最后还应注意到一项“软性”的制度设计,即行长的选择。从1966年的第一任行长渡边武开始,亚开行的行长一直来自日本。其举荐的副行长则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域外,比如美国;近年来自域内国家的副行长数量也逐渐增多。这一方面是亚开行对其区域特征与国际影响进行平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对历史和国际现实的承认与反映:亚开行的设想和孕育都主要发生在日本,最初甚至与日本向东南亚各国提供的援助一样,是战后日本重启和平友好外交的手段,具有深深的日本烙印;而基于上世纪60年代的现实,亚太地区国家仍处在贫困、欠发达的境地,开发银行的股本缴纳很不充分,实际运作一定程度上要依赖域外一些发达国家以及国际融资、债券等方面的资金来源。这些历史现实因素,深深地嵌入到亚开行的制度或“习惯”当中,也塑造了亚开行的行事风格,影响了它在国际舞台上呈现的面貌。三、余论:从亚开行到亚投行
从有设想以来,亚投行与亚开行的关系就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到今天,学界已基本形成统一的看法,认为亚投行的创设是对亚开行工作的“补充”、两者在相关领域有巨大的合作空间,等等(石晋,2016;王吉、李正明,2016)。本章拟更换角度,从亚开行所处的历史现实与相应的局限说起,指出亚开行不仅为亚投行“留出位置”,更是在逻辑、历史、经验各个层面为亚投行这样机构的创设做好了准备和铺垫。
前已述及,亚开行的创立不只是那时相关工作者的理想的投射,更是对当时现实问题和国际形势的反映与应对。从这个角度说,亚开行其实与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开发银行可以划为一类:它们都是在二战后建立的开发银行,主要面对的历史任务是重建战后世界,包括恢复战争造成的破坏和完成被殖民国家地区的开发建设;它们,尤其是它们中那些区域性的开发银行,都在资金方面有明显的紧迫,初始实缴资本都不足法定资本的10%,大部分只在4%上下(陈伟光等,2017);也正因为亚太地区当时尤其突出的贫弱特征,亚开行这样的银行比其他银行更需要域外公私资本的支持,在维护本地区特征的同时必须更多地兼顾域外成员体的权益,从亚开行建立以来域外成员体的总投票权都在35%左右;而同时代的非洲开发银行甚至给域外国家40%以上的投票权,均远高于今天亚投行规定的25%。另外,一些细节也展示出亚开行资本的不足造成的业务特点,前述亚开行第一次改革后开始关注技术援助、并着手建立知识信息库就是一个例子;亚开行在实际提供资金支持方面“作用有限”,也是学界比较公认的一个事实(麦考利,2020:7)。

图三:ADB chief attends press conference,
图源:https://en.yna.co.kr/view/PYH20230502052700315
日美主导关系也是其对国际政治现实的一个反映。不管是股权和投票权的高度一致,还是在行长、副行长等重要行政职务的人选问题上,我们都能清晰看出这两国的同盟以及共同对亚开行工作的主导。事实上,那个时代的多边开发银行中几乎都能看到二者的这种“共同利益”关系;在学者梳理的数据中,能看出在世行、亚开行、欧洲投资银行中美国和日本占据的巨大股权和投票权,以及相应地占据很少份额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陈伟光等,2017)。 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投资亚洲建设的国际机制,亚开行深深地受制于那个时代的国际社会的现实。当这种现实被亚开行设计者以制度的方式确认下来,这固然有利于亚开行适应那个时代的现实并凝聚力量、发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导致半个世纪前的“现实”深深嵌入到这一组织中,成为当今国际世界中的一个“历史遗存”,虽然经历过前述的几次改革和灵活的业务重心调整,也难免与当今这个时代显现出一种“错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投行的特质就凸显出来了;或者不如说,如果把视角放在机构的制度设计和对现实政治的反映这一方面,我们天然地会认可,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共识凝结的成果,也是行事风格迥异的国际行为体。近年的学者将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划分为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主要依据如,这些新的多边开发银行建立在21世纪全新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之下,承认了一批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话语权,将它们纳入世界经济治理者的范围中;资本来源相对更加宽裕,成员体在创始时实际缴纳的股本在亚投行是20%(19630百万美元),在新开发银行达到惊人的50%(50000百万美元),其中中国所缴占很大部分(陈伟光等,2017)。这使得它们对于通过债券、融资来获取域外和非成员体资本没有那么依赖,充足且可自主支配的资金使得其运作具有更大的自主性,支持了比如亚投行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设计初衷,成为比陷入种种限制中的亚开行更直接、高效、有活力的投资银行。 总而言之,历史上,亚开行作为第一家亚太地区的区域性多边投资银行,将世行等全球多边投资银行的经验比较好地吸收、消化和调整,运用在了区域投资银行的建立和亚太地区的投资建设中;同时,在任务目标和制度设计方面切实考虑了现实政治环境的因素,并在半个多世纪的运作中灵活调整、勇于改革,为亚太地区发展最迅猛的时段持续赋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不管是理念还是经验上,它都是本地区新型开发银行比如亚投行的“必要前置步骤”。
参考文献
[1] [澳]彼得·麦考利著,刘天佑等译:《打造亚太美好未来:亚洲开发银行50年史》(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2] Asian Development Bank,"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Charter)",1966,Manila,网址: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institutional-document/32120/charter.pdf.[3] Asian Development Bank,"Number of Assigned Positions in Field Offices",31 December 2022.[4] Asian Development Bank,"Annual Report 2022",网址: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institutional-document/872636/adb-annual-report-2022.pdf.[5] 陈伟光、王欢、蔡伟宏:《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中的亚投行:一个比较分析框架》,《当代财经》2017年第7期,第46-57页。[6] 石晋:《亚投行与亚开行的职能错位与融合》,《现代商贸工业》2016年第13期,第95-96页。[7] 王吉、李正明:《争锋还是共济?——基于亚投行的中美博弈分析》,《改革与开放》2016年第4期,第21-23页。[8] 《亚洲开发银行》编写组:《亚洲开发银行》,北京: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教师:刘莲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副教授)
助教:黄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生)
编辑:余鸿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本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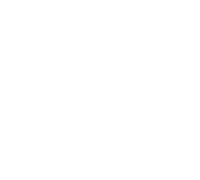




请先 登录后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