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聿東:數字經濟發展亟需監管轉型
來源:北大國發院主辦第五屆國家發展論壇
數字經濟和監管都是當下熱點問題,我隻分享兩點:一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态勢趨勢;二是在這種态勢趨勢下,我們需要什麽樣的監管制度來引導數字經濟健康發展。
中央提出要統籌“兩局”,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可以說,“兩局”都離不開數字經濟,數字經濟是“兩局”的題中應有之意。
就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來講,以數字經濟爲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是大變局的核心體現;從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來看,在傳統經濟增長動能不斷衰竭的情況下,數字經濟作爲新動能可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提供最主要的經濟基礎。
數字經濟的發展态勢和趨勢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作用下,在移動互聯網日益普及和第五代移動通信(5G)商用不斷擴大的趨勢下,以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大數據爲底層數字技術推動的數字經濟正在全球蓬勃發展,對人類生産、生活和生态都産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2019年底,47個主要經濟體的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1.8萬億美元,同比名義增長5.4%,高于同期全球GDP增速3.1個百分點,爲全球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
從數字經濟規模來看,2019年,美國以13.1萬億美元位居第一,中國以5.2萬億美元穩居第二,中美數字經濟差額爲7.9萬億美元,比兩國7.3萬億美元的GDP差額略高一點。此外,德國、日本、英國的數字經濟規模分别位居第三至第五位。這5個國家數字經濟規模,約占全球47個經濟體數字經濟總量的78%。
就數字經濟占經濟總量比重來講,德國、英國和美國這一比重分别爲63.4%、62.3%和61%,而中國爲36.2%,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51.3%的水平。但中國數字經濟增速快,2002-2019年中,年均增長率高達22%,而美國1998-2017年年均增長率爲9.9%。可以說中國數字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都起到了巨大支撐作用。此外,中國“數字人口”最多,數字技術應用場景廣泛,數字經濟發展前景廣闊。
數字經濟正在改寫和重構世界經濟的版圖,也造就了一批“巨無霸”式數字企業。10年前,世界公司市值前10名中隻有微軟一家是數字企業;2020年有7家數字企業如微軟、蘋果、亞馬遜、字母表(谷歌母公司)、臉書、阿裏巴巴、騰訊,非常耀眼地跻身于前10名榜單中。
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增加值)爲35.8萬億元,占GDP比重爲36.2%,可謂“三分天下有其一”。預計2025年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将達到60萬億元,占GDP比重至少可達到“半壁河山”的程度。
面對數字經濟的崛起及對中國的重大機遇,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做大做強數字經濟”,建設“數字中國”和“智慧社會”。中共中央“十四五”規劃建議60條中,其中第15條就是“加快數字化發展”,提出推動産業數字化和數字産業化,推動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争力的數字産業集群,加快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等。在總共60條的規劃建議中,專門辟出一條闡述數字經濟,并将數字經濟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來闡述,足見中央對數字經濟的重視。其實《建議》中其它各條規劃很多也包括了數字經濟的相關内容,如“促進平台經濟、共享經濟健康發展”“穩妥推進數字貨币研發”“建設智慧農業”“實施文化産業數字化戰略”等。
如果說中國曆史上痛失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遇,使中國經濟陷入了積貧積弱的落後局面,可喜的是,對于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生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和當下正在發生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政府敏銳地捕捉到并自覺利用了這種戰略機遇。自2013年以來,中央及有關部門已經就數字經濟發展的相關領域和環節制定了上百個規劃和指導意見,各個省份也在緊鑼密鼓地加快數字經濟布局。可以預見,随着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戰略規劃的部署和實施,中國經濟将會加快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升級的“經濟結構變遷”過程,加速破解一直困惑大多數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難題,由此大大加速中國經濟的趕超進程,最終實現“變道超車”。2019年,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與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共同發布的《中國2049》報告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将在2030年趕超美國。2020年,日本經濟研究中心(JCER)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将在2028年或2029年超過美國。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2020年預測,中國GDP在2024年将達到28.25萬億美元并超過美國。可以說,脫離數字經濟的巨大支撐和拉升,“中國超越”的美好願景是很難實現的。
監管轉型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我們看到,數字經濟“未來正來”。捕捉發展數字經濟已是大勢所趨,更是未來經濟和社會各個領域的“新制高點”,爲此各個國家紛紛把發展數字經濟上升爲國家戰略。随之而來的問題是,在大力發展數字經濟過程中,政府監管應該進行怎樣的創新?畢竟,數字經濟的産生機理和運行邏輯都大有别于傳統經濟,繼續沿用傳統監管體系可能會損害數字經濟的發展活力,正如李克強總理在2017年6月2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所言:“如果仍沿用老辦法去管制,就可能沒有今天的微信了”。現實中種種教訓警示我們,代表先進生産力的數字經濟與相對滞後的監管體制之間的矛盾将是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政府監管隻有主動适應數字經濟的運行規律,才能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一句話,經濟在轉型,監管如何轉型?這是當下現實意義特别突出的重大課題。
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實施凱恩斯主義而陷入經濟滞脹的泥潭,于是供給學派應運而生。供給學派的三大基本主張之一就是放松監管。因此,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和衆多發展中國家紛紛進行了放松監管取向的改革,放松監管的主要内容包括競争化、民營化和簡化監管。經過放松監管的實踐,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監管指數由1982年的5.45下降到2013年的2.09。伴随着放松監管的進程,經濟增長、價格、服務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效。OECD的實證數據充分表明,較高的監管程度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下行影響,這意味着如果放松監管和增強市場競争,就可以實現更高的、穩健的和可持續的增長率,特别是放松監管可以使得傳統壟斷行業“化腐朽爲神奇”,使其成爲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美國曆史上的幾個重要增長期都是發生在政府放松監管時期。20世紀20年代,美國柯立芝政府對市場經濟運行基本保持緘默,創造了以汽車和電力等行業迅速發展拉動國民經濟的“黃金增長期”,史稱“柯立芝繁榮”。20世紀80年代,裏根總統提出,除非監管的潛在收益超過了監管的社會成本,否則監管行爲就不應該發生,其放松監管的一系列大刀闊斧的舉措使美國走出了長期滞脹的泥潭,赢得了“裏根經濟學”的美譽。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和21世紀初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的放松監管程度接近裏根政府時期,美國經濟出現了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長久的繁榮景象。2017年特朗普執政後,把監管看成是“隐性稅收”,承諾“将以創紀錄的速度減少監管”,要求政府“增一減二”,即“每發布一條新規定,就要先廢除兩條舊規定”。
一般說來,監管是市場失靈的産物,即監管是競争的剩餘。社會資源配置要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和競争基礎性作用,“相競而進,相争而奇”,競争才能獲緻繁榮。長期以來,從壟斷行業放松監管的進程和國際比較來看,中國監管指數不僅大大高于西方發達國家,同時也高于新興工業化國家和金磚國家平均水平。
中國數字經濟尚處于發育和成長階段,監管是必要的,但更多的是審慎包容監管。如若任憑金融領域的“穿透式監管”蔓延到各行各業,就會造成《“十三五”市場監管規劃》中所批評的“人盯人、普遍撒網”的“煩苛監管”和“無限監管”現象,不僅可能導緻“監管失效”,而且可能贻誤發展機遇。正如李克強總理2016年5月在全國“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電視電話會議上所指出,“煩苛管制必然導緻停滞和貧困,簡約治理則帶來增長和繁榮”。爲此,2017年國務院印發了《“十三五”市場監管規劃》,提出要改變傳統“管”的觀念,把激發市場活力和創造力作爲市場監管的重要方向,要适應新技術、新産業、新業态、新模式蓬勃發展的趨勢,提出實行簡約監管、包容監管、審慎監管、智慧監管等原則,這爲中國監管轉型提供了明确方向,更爲數字經濟監管轉型提供了基本指南。
需要強調的是,我不是說要取消監管,也不是說要強化監管,而是要讨論監管轉型問題。時間關系,這裏隻是指出監管轉型的方向,不再展開。第一,總體上從強化監管轉向放松監管;第二,結構上從經濟性監管轉向社會性監管;第三,方式上從歧視性監管轉向公平競争監管;第四,内容上從“正面清單”監管轉向“負面清單”監管;第五,流程上從前置審批制走向後置監管制;第六,機構上從專業性監管轉向大部制監管;第七,手段上從“人盯人、普遍撒網”式監管走向“監管沙盒”,不斷創新監管手段。
最後,我想說的是,過去未去,未來已來,當下我們正處于“曆時性共存”的時代,無論對于個人還是組織,難免出現失落、迷茫和憧憬的“三感”疊加狀态。但無論如何,我們仍要擁抱數字化時代,堅定對數字經濟光明前途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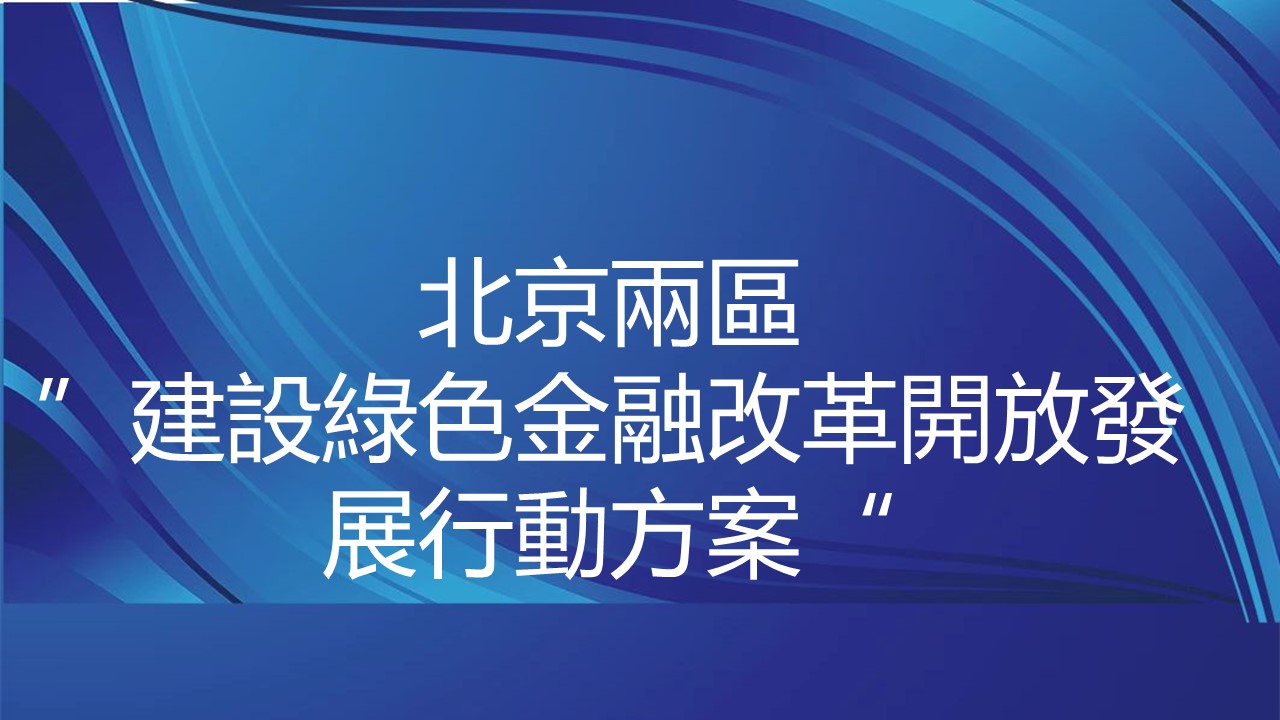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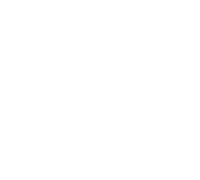




請先 登錄後發表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