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超低利率新常态——全球貨币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李揚:超低利率新常态——全球貨币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來源:《北大金融評論》第7期
記載全球超低利率(負利率)發展動态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有四。
20世紀90年代,全球利率(以美國爲例)終于越過1981年的16.39%的高峰,于1992年回落至5%以内,全球進入低利率時期。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迅速蔓延至歐洲,觸發當地主權債務危機,随後全球債務危機爆發。爲應對愈演愈烈的債務危機,美聯儲迅即将其官方利率降至0~0.25%,且持續4年。随之,世界主要國家貨币當局紛起效仿,全球進入超低利率時期。
2012年,丹麥央行爲應付持續惡化的經濟頹勢,首次推出負利率貸款,更是宣布了全球超低利率(負利率)時期的到來,人類社會“從此進入了一片未知領域”。
2021年2月至3月,全球疫情開始緩和。然而,日歐美央行卻相繼發表貨币政策聲明,繼續保持負利率(日本央行和歐洲央行)和零利率(美聯儲)不變,同時加碼了量化寬松的力度,全球超低利率(負利率)的格局仍在持續。
利率長期超低甚至爲負,異乎尋常。自有金融以來,正利率便構成金融正常運行的基石和持續發展的動力——因有正的利率,金融才得以産生,金融産品和金融服務方能在種類和範圍上不斷拓展;因有利率爲正,銀行等金融機構方能存活和發展。顯然,利率超低(負利率)對金融運行的傳統秩序以及我們一直奉爲圭臬的主流金融理論和政策都提出了挑戰。
實體經濟運行體制機制的變化,是利率走低的基本因素。全球利率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擺脫其長期高懸的格局,并于90年代初期回落至5%之内,根因之一在于,期間世界的發展進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亞洲“四小龍”“四小虎”相繼崛起、中國于90年代開啓市場化改革進程、蘇東集團于90年代前後解體并全面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等。這些變化深刻改變了世界,其中全球勞動力供求格局的巨變讓全世界收獲了長達二十年的人口紅利。IMF曾在研究中指出,80年代後期以來,由于勞動力變得日益全球化,全球有效勞動力供給在1980~2005年間增加了3倍。從時間分布看,有效供給的增加主要發生在1990年以後;從地區分布看,有效供給的增加約有一半多來自中國等東亞國家,其他則可歸諸南亞、前東歐集團國家和非洲、拉美地區國家。分析顯示:正是全球人口紅利的釋放,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時期。這個時期經濟運行的典型特征就是“三高兩低”: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低通脹和低利率同時并存。
然而,“大緩和”隻是故事的上半段。2001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的破滅,以及接踵而來的美國次貸危機、歐洲主權債危機等,則開啓了整個故事的下半段。這個目前仍在持續的過程,連同此前長達20餘年的“大緩和”時期,共同構成了“百年不遇之大變局”的豐富内容。
20世紀90年代便已形成的全球總儲蓄長期超過總投資的格局,在新世紀中仍在持續,并決定了自然利率長期向下的趨勢。隻不過,上世紀的人口紅利,此時已悄然轉變爲“人口負債”。其中,中國人口結構的加速惡化,成爲主要貢獻因素。進入“人口負債”階段後,經濟通常會在兩個方向上失去增長勢頭:生産力下降和社會負擔加重。“人口負債”下,工資率上升、潛在生産率下降、老齡化惡化并帶來社會支出提升、資本積累減少,“三高兩低”中的“三高”漸次失去,僅餘“兩低”還在頑強地表現自己。換言之,表現在貨币金融領域中的長期超低利率現象,實則隻是實體經濟長期衰退的金融表征。
在諸多導緻自然利率趨降的實體經濟因素中,人口結構惡化和技術進步趨緩是主因。在全球老齡化的背景下,全球勞動人口增長率、安全資産收益率在過去30~50年中均處于下行趨勢,直接引緻了全球自然利率下行。而由于近幾十年來全球尚未出現“颠覆性”科技進步,全球全要素生産率(TFP)的增長率亦趨于緩慢下降。數據顯示,自21世紀初互聯網泡沫破滅以來,全球技術進步的速度已落在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期間的平均水平之下。
金融周期的影響。對于經濟活動日益以金融活動爲中心,以金融關系爲紐帶,以金融政策爲協調工具,從而把金融作爲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來推動經濟發展的這一過程與趨勢,我們将其稱爲經濟的“金融化”。20世紀末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實體經濟不斷被“金融化”的現象,從而使得金融周期逐漸成爲主宰經濟運行的主要動力。
從源頭上說,金融工程的出現以及相應的資産證券化的廣泛推行,完美地解決了實體經濟運行中經常出現的期限錯配問題,引導了經濟的“金融化”進程。這一革命性進展最早大規模出現在住宅金融領域。抵押貸款證券化顯著提升了住房市場的流動性,而其原理也在大範圍複制和推廣,催生了各式各樣的資産證券化。正是這些證券化産品,構成發達經濟體影子銀行體系的主體,其規模如今已達到貨币當局不可忽視的程度。
經濟“金融化”不斷提高的事實,還可以從各個金融領域的發展及其同實體經濟的關系變化中觀察到。例如,經濟的證券化率(各類證券總市值/GDP)上升、金融相關比率(金融資産總量/GDP、M2/GDP等)不斷提高,證券市場年交易量、信貸餘額、年保費收入、外彙日交易量等對GDP的比率穩步上升,貿易相關的資本流動與非貿易相關的資本流動的比率不斷下降(上世紀末已達1:45)等,都是經濟“金融化”的适例。
毫無疑問,經濟“金融化”程度不斷提高,正逐步改變着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使得債權/債務關系、委托/代理關系、風險/保險關系等金融關系,逐漸在經濟社會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并深刻地改變着我們的經濟運行。
“金融化”對貨币政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它使得貨币政策向實體經濟傳導的渠道發生了變化,主要表現爲:傳統上,貨币政策主要通過影響商品與勞務的價格(物價)和實體經濟的資金成本(利率)發揮作用;經濟“金融化”情況下,當貨币政策尚未來得及展示其對物價和資金成本等實體經濟因素的影響時,金融産品等“虛拟”産品的價格便已發生即時和劇烈的變化,并通過改變經濟主體的資産負債表的平衡關系,改變經濟主體的行爲方式。鑒于此,貨币政策不得不越來越關注金融資産的價格變動,不得不越來越多地将政策重點置于壓低利率方面。
貨币政策操作範式。基于貨币政策操作的分析,能進一步解釋超低利率背後的人爲因素。這方面的進展,與金融界持之以恒地對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展開研究密切相關。至今,學術界和政策界已經在很多方面達成了對大蕭條原因的解釋。其中,大蕭條的深刻教訓是,在全社會都急切需要流動性的最緊急狀況下,中央銀行卻囿于“真實交易”原則且将減少金融風險作爲最優先事項,未能及時向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救助商業銀行和企業,緻使危機愈演愈烈,終至演變成幾乎使資本主義制度滅亡的大蕭條。這種認識,深刻地改變了央行調控的邏輯和行爲方式,并因一批精研“大蕭條”的專家(如本·伯南克等)入主央行而從根本上改變了其行爲方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發達國家貨币當局毫不猶豫相繼推出超低利率和量化寬松等新型貨币政策工具。2020年以來,爲應對新冠疫情影響,他們更将應對危機的政策推向極緻,一方面允諾向經濟主體直接提供支票,增加各類經濟主體的資金可得性;另一方面,索性直接實行負利率政策,進一步降低經濟主體獲取資金的成本。
總之,鑒于以上三大因素均繼續存在并發揮作用,全球超低利率乃至負利率将在大概率上成爲金融運行的長期現象。

長期超低利率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比較複雜,可以從經濟主體、市場和宏觀調控當局等九個層面加以分析。
企業。企業是超低利率的受益者,因爲其貸款可得性和融資成本都将得到改善,企業獲得循環貸款、貸款展期的機會也會增加。但在支持實體企業的政策導向下,商業銀行很可能錯配資金,爲高風險、盈利能力很差的“僵屍企業”提供“常青貸款”。日本和歐洲地區的14個發達經濟體在推行負利率政策之後都出現了“僵屍企業”數量增加的現象,我國原已存在大量虧損企業和“僵屍企業”,也都在低利率的政策環境中得以存活。
居民。在收入不增加的條件下,超低利率會使居民減少消費,同時減少投資性儲蓄,但可能增加預防性儲蓄;在投資一端,居民更傾向于尋求高收益、高風險投資,如私募基金等,同時,也傾向于追求更爲個性化的金融資産。值得憂慮的是,在正常情況下,居民收入的相對下降本應導緻儲蓄率下降,而目前的情況是,居民儲蓄率不降反升,這樣一種格局,将導緻貨币當局的救助政策效力遞減(居民獲得補助後“不花錢”)。這是反危機政策最不樂見的結果。
商業銀行。超低利率對商業銀行的淨利差有再分配效應,以利息收入爲主要盈利來源的商業銀行受負面影響較大;而主要依靠提供服務等非利息收入的銀行則受損較小,相反,因其提供服務的資金成本下降,反而可能獲利。我們的初步研究顯示,在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商業銀行受超低利率(負利率)的影響較小,主要原因就在于,這些國家的商業銀行早就完成了銀行從“産品推銷者”向“服務提供商”的轉變,而且大多采取混業經營模式,它們的盈利主要得自服務收費和市場交易,息差收入占比較低。
非銀行金融機構。非銀行金融機構是超低利率(負利率)的受益者,因爲它們原本就較少依賴息差收入,主要依靠向非金融部門提供各類服務和參加證券市場各類交易賺取收入。本世紀以來,歐美日等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均有較大發展,而且,随着影子銀行的迅速發展,商業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界限進一步模糊了。
政府(财政)。短期内,超低利率或将誘發政府債務過度擴張,造成潛在新的财政風險;長期來看,市場投資将共同推高主權債務的風險溢價,反而約束了政府債務的過度擴張。值得注意的是,超低利率長期持續,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政府債務擴張的邏輯。理論上,如果可以不斷借新還舊,本金并不構成政府債務政策的限制,而是利息償還将成爲債務的限制。隻要國債付息占GDP比重和占政府支出比重不呈上升之勢,則政府的債務融資幾乎可以無限制地持續下去。這種情況事實上已經發生了。資料顯示,美國政府現在每年支付的國債利息接近6000億美元,但自1990年代以來,全球曆史性的低利率,使得國債利息占GDP的比例大體保持穩定。因此,雖然美國債務占GDP的比重自1990年以來一直逐步走高,但由于利率持續走低,國債利息占GDP的比例已經創至少30年來的新低。由此可以看到,超低利率與财政赤字之間已經形成高度内洽的關聯。這種狀況如果持續,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将高度一體化。
央行。負利率政策弱化了貨币政策傳導效果,使得央行越來越需要把各類資産市場的動态納入視野,其貨币政策邏輯将經曆根本性變化。同時,負利率的施行也使央行的獨立性受到削弱,央行資産負債表風險暴露增加。從體制上說,中央銀行需要在降低政府債務負擔與未來通貨膨脹之間,在支持政府債務融資和保持央行獨立性之間,困難地尋求平衡。更重要的是,由于超低利率、政府債務、債務貨币化等越來越深地契合在一起,兩大政策體系的協調配合可能進入新的格局。
固定收益市場。固定收益産品的收益率随超低利率出現而下降,其投資吸引力下降,這對此類市場的發展不利。同時,以固定收益産品(如政府債券等)爲主要投資對象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人壽保險公司、養老金、貨币市場基金等)的盈利也會受到負面影響。他們會逐步減持固定收益産品,尋求其他風險更高的資産增值之道,使得自身行爲變得更具冒險性。
資本市場。股票市場因能獲得源源不斷的低成本資金,其價格便有了上漲動力。但是,超低利率也意味着經濟下行趨勢延續,上市公司的盈利狀況趨于惡化,故而股市泡沫可能上升。
金融穩定。超低利率不利于金融穩定,具體表現在:金融中介體系更具冒險性;非金融企業的杠杆率會繼續攀升;長期負利率會使央行貨币政策環境發生變化,可能在不知不覺中使其政策導向從逆周期的初心轉變爲順周期的結果,從而加劇金融不穩定。
四、對中國的影響及對策建議
大緻上,超低利率(負利率)對中國的影響,可以沿着如下三個方向展開分析。其一,全球的長期超低利率和負利率格局惡化了中國的國際環境,特别是國際金融環境。這将通過多重渠道對中國産生負面影響。其二,目前中國還是唯一的保持正常貨币環境的國家,利率仍保持正的水平,就使得中外息差成爲套利對象。息差導緻人民币彙率堅挺,引緻資本内流,其利在于可以活躍中國資本市場,助力人民币國際化,其弊在于可能引緻國内金融波動,這将考驗我們的管理能力。其三,中國目前固然仍保持着較高的利率水平,但由于經濟增長下行趨勢依舊,加上疫情長期化,未來一個中期内,利率下行的壓力比上行的壓力要大一些。果若如此,主要靠吃息差存活的中國商業銀行就會受到極大的沖擊,中國的金融結構将因此面臨極爲巨大的調整壓力。
面對全球超低利率(負利率)趨勢,中國必須高度警惕,全面布局。其中,如下五者最爲重要:
一是在向雙循環新格局轉型的過程中,貨币政策應該更爲關注中國經濟的内部均衡,不應簡單與發達國家競争或追随其政策,更不宜爲維持外部均衡而犧牲内部均衡。同時,在全球經濟仍在下行時期,應着眼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合理使用降息空間,更多使用結構性政策工具。
二是應當有效監測跨境資本流動,謹慎、有掌控、有次序地向外國資本開放金融市場。宜運用延長申購期限、适當控制中标率等經濟手段,有效調控外資進入中國債務市場的速度、規模、節奏和領域,維護國内金融安全。
三是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關注國内人口增長率、資本/勞動比、全要素生産率等影響利率的核心因素的實體經濟因素的變化。通過加速創新、延遲退休、鼓勵生育等政策,減緩勞動人口增長率下降的速度;要改善企業之間的資本錯配狀況、加快創新技術的應用等以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等,從根本上扭轉或緩釋自然利率低迷的傾向。
四是加速國内金融改革。一要推動商業銀行改革,重點方向是加速商業銀行向服務業轉型、在盈利模式上減少對息差的過度依賴,同時穩步推動商業銀行向混業經營模式轉型。二要推動養老金機構改革,考慮在個人賬戶中引入可變利率、可變負債、可變年金等。三要大力發展保險業。四要鼓勵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同時,盡快将非銀行金融中介的活動納入金融綜合統計和宏觀調控視野,以更爲準确地識别中國的金融周期及其對利率的擾動,提高利率調控效率。
五是深化“三率”(人民币彙率、利率、國債收益率)市場化改革。彙率決定的是資源和市場在國内外配置的比較優勢,關乎新發展格局的形成和發展;利率的水平及結構,決定了資金在國内哪些地區、部門、産業中被使用的優先順序,關乎國内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國債收益率曲線涉及所有金融産品的定價問題,構成全部金融産品的定價基礎。20餘年來,我國在“三率”市場化改革方面已取得較大進展,但關鍵步伐似乎尚待邁出。我們認爲,積極探尋貨币政策與财政政策協調配合機制,在央行和财政部精誠合作的基礎上推動“三率”改革,或許是今後的改革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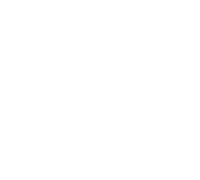




請先 登錄後發表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