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視角 | 余永定:關於宏觀經濟問題的幾點看法
截至1月25日,除天津外,我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已為2022年設定了經濟增速目標。其中,北京設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在5%以上,上海、山東、廣東等8地將增速設定在5.5%左右或以上,其餘大部分中西部省市將目標設定在6%-7%,海南目標定得最高,為9%。各地公佈的2022年經濟增速目標為觀察中國今年經濟走勢提供了一定的參考意義。從去年來看,在2020年低基數效應影響下,2021年中國GDP同比增速高達8.1%,遠超6%的目標。但隨著低基數效應的消退,市場普遍預期2022年中國經濟增速大概在5.5%左右。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撰文指出,只要不存在通貨膨脹失控的危險,只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我們就應該把經濟增速定的盡可能高一些。”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穩增長”目標,餘永定認為,在目前的語境下,“穩增長”應該是遏制經濟增速的進一步下跌。對於如何保持宏觀經濟大盤穩定,餘永定認為,在經濟持續下行、預期不振的情況下,推動經濟增長只能主要依賴基礎設施投資,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增速的提高創造“擠入”效應,帶動製造業投資,並通過對經濟增長的刺激帶動消費需求的增長。
關於宏觀經濟問題的幾點看法
文 | 餘永定
第一,我們應該對中國2021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有一個比較客觀、準確的認識。2021年中國GDP增速8.1%。如何看待這一經濟增速?高於8%的增速是否表明2021年中國實現了較高的經濟增長呢?我們可以同疫情前的2019年經濟增長速度比較一下。同比會涉及到基數問題,環比則不直接涉及基數問題。我們可以比較一下2019年和2021年各個季度的環比增速。2019年4個季度環比增長速度是1.6%、1.2%、1.3%和1.6%,相應的年化增長速度6.6%、4.9%、5.3%和6.6%。而2021年4個季度的環比的增長速度年化之後幾乎都明顯(除第四季度)低於2019年。不難推斷,如果扣除基數效應, 2021年的經濟是運行在低於2019年6%的水準的。在假定不發生疫情、2020年正常增長的情況下,2021年GDP的增速恐怕就要低於5%。所以,我們要客觀看待2021年超過8%的經濟增速。簡言之,我們現在的經濟增速是低於“潛在經濟增速”的。雖然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相信任何人知道,但從產能利用、物價和就業水準等方面來看,可以認為多年來中國經濟是低於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
第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經濟是處於低通脹甚至是通貨收縮狀態的。例如, PPI(生產價格指數)從2012年3月開始連續54個月都是負增長,而直到2021年前兩個季度,我們的CPI和PPI都是不高的,平均來說 CPI在過去10多年大概不超過2%。2021年下半年物價特別是PPI上漲較快,但最新的數字顯示,目前在CPI繼續保持低水準的同時,PPI已經開始回落。
沒有通貨膨脹,甚至出現通貨收縮,這說明,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實際上是可以進一步提高的。永遠不要忘記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這一至理名言。沒有發展,什麼都談不上。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也完全可以說,“增長是硬道理”。增長不是一切,但沒有增長就沒有一切。
我們當然應重視“增長的品質”,但沒有數量就沒有品質,脫離增長就談不上高品質。在現實中,如果經濟低迷,則結構改革、技術創新和共同富裕等工作的推進就都會變得十分困難。順便說一下, 提倡“高品質增長”是完全正確的,但100萬億元GDP就是100萬億元GDP。理論上,在GDP之間不存在品質孰高孰低的問題。在宏觀經濟層面,我們必須假定所有GDP是同質的。否則,同一國家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同一時期的GDP就無法比較了。在產品和專案的層面,確實存在只顧數量不顧品質的問題,這樣的經濟活動可能根本不創造價值。如果這些經濟活動的產物也被計入了GDP,就說明我們的市場、監管和統計出了問題。但這些問題並不能通過降低GDP增速來解決,解決這些問題也並不一定要以降低GDP增速為代價。
第三.我認為,經濟學界在討論是否應該爭取獲得一個較高的增速時存在著許多重要的方法論錯誤。我想簡單討論一下這個問題,例如,有觀點認為,中國面臨很多結構性問題,較高的增速不現實。不能說這種觀點沒有一點道理。但“較高”是多高?是10%、8%、7%、6%、還是5%?。2010年第一季度12.2%,肯定太高。2019年GDP增速降到了6%、2022年爭取實現5.5%,還太高嗎?不利的結構性因素充其量能夠說明中國GDP增速為什麼會有所下降,甚至明顯下降,但並不能說明增速到底降到百分之幾才是合理的。
什麼是結構性問題?沒有明確定義。我們習慣上把宏觀經濟之外的所有問題統稱“結構性”問題。可以說,“‘結構’是個筐,所有東西都可以往裡裝”。從我們經濟學家所寫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所謂“結構性”包括:人口老齡化、投資-消費-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民營企業和國企的地位、收入分配不均等、資本市場欠發達,自主創新動力不足、區域經濟不平衡、城市化滯後、服務業占比不高、智慧財產權保護不足、環境污染、資源枯竭、規模收益遞減等等。可以說,宏觀經濟之外的所有的問題,都被同一個詞裝進去了。“結構性”問題的單子可以開得非常長,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問題在於,許多人用結構性因素籠而統之的來解釋我們某個具體年度,甚至具體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用這樣或那樣的“結構性”因素來解釋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7%、6%、或5%。這種以抽象的原因直接推導具體結果的思路在邏輯上是完全錯誤的。“結構性”因素可以用來解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但不能用來解釋年度和季度經濟增速的差別。
中國2010年第一季度是12.2%,從那時開始就在下降,幾乎是每個季度都要下降。如果從12%降到10%這是結構性原因造成的,我們可以接受;那麼,從10%降到9%呢?從9%降到8%呢?從8%降到7%呢?從7%降到6%呢?現在又向著5%的方向下降了,是不是還要用同樣的結構性因素來解釋呢?為什麼就不能用某種宏觀經濟政策來解釋呢?
“結構性”的因素肯定是要影響經濟增長的,但無法解釋經濟增速的年度和季度變化,正如你不能用衰老來解釋為什麼你今天會有血壓高、糖尿病。關於這個問題,我有四點評論。
第一點,所謂結構性因素一般來講是慢變數,是在幾十年的時間內,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影響經濟增長速度。而對於每年、每季度GDP增速,這些因素的影響是極其微小的。儘管其在幾十年中的累積的影響可能很大,但一般而言,在每年、每季度中是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的。例如,人口老齡化無法解釋為什麼中國某個年度或季度經濟增速的下降。
第二點,“結構性”因素數量龐大,同時影響經濟增長。每個因素在不同時期的影響各不相同,但總的來講,在給定的時期內,單個所謂“結構性”因素對GDP增長的影響是微小的。當然,也有特例。如果把“外部衝擊”歸類於結構性因素。疫情就是影響2020年中國經濟增速的最重要原因。
第三點,結構性因素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比如人口老齡化,一般來講,在假設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將導致經濟增長潛力的下降。但其他因素,例如技術進步也在發揮作用。人工智慧、機器人的發展難道不能部分抵消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嗎?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但有什麼根據說這種下降一定會使中國GDP增速由2011年的9.6%下降到2012年的7.9%?同理,由人口老齡化推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一定會低於6%或5%是沒有道理的。
第四點,結構性因素影響短期宏觀經濟變數,要經過一個很長的因果鏈條,必須找到因果鏈條的各個環節,才能確認某個結構性因素對某個年度的GDP增速的具體影響。不僅如此,因果鏈條不是單一、直線的,諸多因果鏈條還會相互交叉、相互影響。直接影響年度、季度經濟增速的的因素是短期宏觀經濟變數:消費、投資、政府開支、進出口等。當經濟增長主要受供給約束時,要分析決定當期供給的供給方因素。結構性因素是通過一個非常長的因果鏈條,才作用到消費、投資等直接決定GDP增速的宏觀經濟變數的。如果想證明某特定“結構性”因素決定了經濟增速只能是6%,那就需要把因果環節一個個點出來。比如人口老齡化(用某種量化指標度量的老齡化程度)影響了A,A又影響了B,B又影響了C……最後作用到消費、投資、淨出口。要逐一識別這些環節。如果根本沒有找到各個環節,就直接跳躍到中國經濟增速只能是6%這樣的結論,在邏輯上就犯了“假推導”、“推不出”的錯誤。
宏觀經濟討論的是短期問題,考慮的時間長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月度。在分析宏觀經濟形勢和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是要假定“結構性”因素給定的。做短期分析的時候,首先要考慮消費、投資、淨出口等具體因素。例如,消費增速減少了,為什麼減少?同什麼因素有關?這樣倒推回去,可能會涉及一系列長期、結構性因素。找出這些因素,有助於判定消費變化的趨勢和運用宏觀經濟政策與其他政策影響消費的可能性。
第四,關於刺激消費的問題。2020年初很多學者認為,可以通過發放政府補貼提振居民消費。通過提高居民消費刺激經濟增長當然是一種可以考慮的思路。但如果消費者長期固定收入下降、對經濟增長前景悲觀,這時即便發了錢,居民可能也不會花出去,而是會把錢存起來。2020年武漢解封之後,有人認為,消費可能出現“報復性增長”。但這種預期並沒有實現。直至2021年下半年,消費也沒有出現報復性增長。經濟理論告訴我們,消費受現實收入以及收入預期的影響。如果我們不能夠首先提高經濟增速、使居民的收入增加,並使居民改變增長預期,實現消費增長就會比較困難。當然,對於因疫情衝擊而導致生活困難的低收入階層必須提供救助,但這不是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而是和諧社會建設問題。
第五,如何確定經濟增長目標。最近中央提出“穩增長”非常及時。在目前的語境下,“穩增長”應該是遏制經濟增速的進一步下跌。但中國應該爭取實現多高的增長速度呢?學界普遍認為,應該首先算出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再根據這種計算的結果來決定GDP增長目標。我在過去很長時間也是這種主張。但問題是,模型過於依賴嚴格的假設,很多基本統計材料闕如,“潛在經濟增速”是很難準確計算的。
在我幾十年的經濟學研究的職業生涯中碰到過很多著名經濟學家,他們因準確預測了某個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或增長趨勢而名聞天下。但實際上他們這輩子可能就准了一次。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是要計算的、這種計算結果也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但確定經濟增長目標時,不能以這種計算為依據。
我特別贊成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錯”哲學:我也搞不清楚結果會是什麼(當然大方向是清楚的),反正咱們先試試看。這種開放式思維方式是很成功的。事實是:有些決策者可能不懂經濟學,但他們管經濟比懂經濟學的人管得好。儘管中國過去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依然維持了40年10%左右的經濟增長。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經濟體量世界排名18,GDP低於荷蘭那樣的“蕞爾小國”。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GDP不足日本的1/4,2010年趕上日本,現在是日本的3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成功了就是好的。
我是20世紀70年代末進入社會科學院的,進去的第一天就聽同事講中國“貨幣超發”、要發生通貨膨脹、要發生經濟危機。大量“超發”的貨幣是“籠中老虎”,“老虎要出來吃人了”等等。我等 “籠中老虎”出來,等了40多年,頭髮都等白了。如果當時的決策者像我們這些研究人員所希望的那樣,小心翼翼,不敢冒險,可能就不會有後來的高速經濟增長、就沒有今天的中國經濟了。經濟學不是一種確定的科學,在一定程度上是藝術。我一直有一種感覺:幸好當初政府沒聽經濟學家的一些中規中矩的意見。如果聽了,中國經濟增速估計就沒有後來保持了近40年的平均10%的經濟增速了。
世界銀行在20世紀80年代寫了不少預測中國經濟發展的報告。現在再去讀那些舊報告就會發現,這些報告的預測大多同中國後來的實際發展相差甚遠,有的可能還是“南轅北轍”。撰寫報告的世行專家都是當時最優秀的經濟學家。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結果?因為世界太複雜、中國太複雜、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太大。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經濟發展規律瞭解得非常少,必須抱著非常謙卑、隨時準備糾正錯誤的態度來制定和執行經濟政策。
第六,我以為,經濟增長目標的確定應該建立在經驗-試錯的基礎之上。如果執行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導致通貨膨脹失控、金融脆弱性嚴重惡化,就需要降低經濟增速目標。如果通貨膨脹並沒有失控,金融脆弱性並沒有那麼嚴重,就應該採取更具有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爭取實現盡可能高的經濟增速。2019年我提出保6%的主張。正如我一再強調的,6%具有象徵性意義。我的核心觀點是,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開始基本上是逐季下降,2019年已經跌到6%,這種情況不能繼續下去了。事實上,當時中國的通貨膨脹率相當低;雖然杠杆率比較高,但金融體系基本上還是健康的。中國依然有比較大的政策空間,為什麼不能嘗試實現更高一些的經濟增速呢?在沒有進行嘗試之前,就認定中國必須讓經濟增速一步步降下來是錯誤的。經濟增速長期下滑會產生所謂的“磁滯效應”(hysteresis effect):經濟增速長期、持續下滑,就會出現以後想快也快不起來了的結果(工人長期失業難以重新就業、團隊解散後就難以重新組織)。聽任經濟增速下滑、聽任投資增速下滑,經濟增長潛力就必然下降。其結果與其說是經濟增速不得不下降,不如說你認為它必然要下降,於是它就下降了。
總之,只要不存在通貨膨脹失控的危險,只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我們就應該把經濟增速定的盡可能高一些。
目前,市場對中國通貨膨脹失控的擔心已經明顯減弱,但對於金融風險的擔心還是比較強烈的。我以為,長期以來,外界對中國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估計的過於高了。年年都有很多人預測中國要發生金融危機,單從2008年之後就可以列出一張長單。2012年春節之前,我隨北大到紐交所交流。當時很多美國人認為中國房地產市場要崩潰、溫州的地下金融要把中國的整個金融體系拖垮,還有“影子銀行”問題。我們則向紐交所的人解釋:這些問題都存在,但根本不可能使中國出現大的金融危機。例如,溫州地下金融的規模和中國整個經濟相比,實際上九牛一毛。我們應該關注它,不能無視它,但它不會造成部分人所認為的那樣的危機。
第七,增速不僅是個經濟問題,而且是個地緣政治問題。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上升,我們在下降,增速差距正在縮小;印度的增速已經連續兩年超過中國。對這樣的問題我們不能無視。從美國一些學者,特別是地緣政治方面的學者最近發表的文章和講話中可以看出,他們很高興看到中國經濟增速的進一步下降。中國是有潛力,也有能力遏制經濟增長速度的進一步下降,是能夠使經濟增速保持在一個較高水準之上的。
第八,中國政府還是應該為2022年經濟增長確定目標。當然,這個目標是引導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必須有個目標,沒有增長目標就難以制定具體政策。實際上,每個部門、各級政府都有一個隱含的目標,只不過沒明說。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公開設定目標?沒有統一和明確的增長目標,各個政府部門和各級政府就難以協調行動。在確定目標之後,我們用試錯的方法嘗試去達成目標。如果目標確實無法實現,我們再退回來也不晚。
第九,維持一定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速是實現經濟增長目標的重要手段。應該可以根據歷史資料和經驗制定明確的增長目標,中國消費、投資、出口所需要實現的增速。宏觀經濟變數中的大部分是內生的,只能根據一定假設去預測它們的增長速度。但是,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基本上是可以由政府控制的。因而,可以根據不同的有關消費、投資(扣除基礎設施投資)、出口增速的假設,計算出為了實現給定的經濟增速目標,基礎設施投資應該保持的增速。當然,計算過程不是能夠一次完成的,可能需要多次反覆運算。無論如何,最終是可以計算出一組最可能實現的,自洽的為實現給定的GDP增速,基礎設施投資所需要實現的增速。
2021年中國基礎設施同比增速僅為0.4%,而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基礎設施投資一般保持在20%左右,2009年6月基礎設施投資累積同比增速高達50.7%。後來,基礎設施投資增速一路下跌,2012年2月進入負增長區間。2013年一度回升到20%以上,隨即又開始持續下跌。2021年全年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增長0.4%,遠低於新冠疫情前3.8%的年增速,甚至不及2020年0.9%的增長。在以往,基礎設施投資增速一直是逆週期變化的,是維持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因素。2021年基礎設施投資順週期下行,又如何不能拖累GDP增速呢?
在經濟持續下行、預期不振的情況下,推動經濟增長只能主要依賴基礎設施投資,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增速的提高創造“擠入”效應,帶動製造業投資,並通過對經濟增長的刺激帶動消費需求的增長。
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否已經超前,沒有更多項目可建了?完全不是如此。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寬廣的概念,它絕不僅限於“鐵公機”這樣的老基建,而是還包含著“新基建”以及一系列軟性公共產品的提供。即便是傳統基建項目,我們依然存在巨大的補短板任務——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死亡失蹤380人(鄭州市)已經充分說明問題。
基建投資沒有收益的說法也是片面的。在正視既有問題、提高投資效益的同時,必須看到,基於基礎設施的功能與性質,基礎設施投資的成與敗不應完全或主要以商業回報來衡量。
基礎設施投資的可控性來源於中國的制度優勢,是其他國家(包括美國)想學習而不得的優勢,放棄這種優勢無異於自廢武功。
不僅如此,由於房地產投資在中國經濟中居重要地位,房地產投資增速下降將拖累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就更有必要提高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速,對沖房地產投資增速下降對經濟增長造成的不利影響。
第十,房地產投資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扮演著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國房地產投資在GDP中的占比是全世界大國中最高的國家,中國房價的增速是全球最快的國家之一。中國房地產的主要問題是資源配置問題,且難於判斷房地產是否有全域性的嚴重泡沫。中國貨幣當局長期處於兩難地位。一方面,希望抑制房價過快上漲。一旦發現房價增長過快,就會有房價調控政策出臺,貨幣當局就會相應退出原來執行的政策。另一方面,房價或房價增速下降則會導致房地產投資增速的下降,並進而導致整個經濟增速的下降——於是房價調控政策被擱置,貨幣政策轉向寬鬆,房價報復性反彈。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經歷了數個這樣的房地產週期。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我國一線城市房價確實過高、上升過快,不利於民生和經濟長期發展。但抑制房價不應該是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目標應該僅僅是增長(就業)和通脹。抑制房價應主要通過房產登記全國聯網和稅收等非貨幣手段解決。
房屋建設中存在嚴重結構性問題。一方面,存在大量空置的高端住宅;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體,特別是年輕人難以解決住房問題,房貸壓力沉重。應該增加廉租房供給,健全房屋租賃市場,逐步消化三、四線城市存量住房。
本輪房地產調控確實存在時機選擇、一刀切等問題,應該調整,但也要避免突然改變方向,造成市場的震盪。
第十一,提高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必須解決融資問題。2008-09年四萬億的重要經驗教訓是:應該主要通過政府發行國債而不是通過地方融資平臺從銀行貸款為基礎設施投資融資。目前,一方面中國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另一方面中國存在發行國債的較大空間。發國債可能是中國解決目前經濟困難的不二法門。發行國債導致利息率上升等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同時,擴大國債發行量對於發展中國資本市場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至於發行國債的具體方式——如地方債應該如何發,是否把專項債改為一般公共債等問題——則可以進一步研究。
2021年中國財政政策偏緊,不利於經濟增長的恢復。從宏觀政策的層面上看,2022年應該明顯提高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政府無需過度拘泥於財政赤字率不應該超過3%的教條。3%的設定並無任何堅實的理論根據。經驗證明,在許多情況下,降低赤字率的最有效方式是提高經濟增速。而提高經濟增速,在短期內可能就不得不增加財政赤字。1996-97年日本緊縮財政的失敗經驗和中國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財政擴張的成功經驗都說明了這點。
第十二,2022年中國應該執行更具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要加強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在經濟過熱時期,貨幣政策可以有效發揮作用。在經濟下行期間,由於“流動性陷阱”之類問題,儘管中央銀行可以且應該通過降息等方式緩解企業和居民財務困難,刺激經濟增長,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會受到極大制約。即便增加信貸、降低利息率,企業和居民的貸款需求可能也不會有很大增加。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可以通過支持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方式發揮作用。
如果大幅度增發國債,國債利息率必然上升,並進而導致金融體制中各類利息率不同程度的上行。這時,降息等擴張性貨幣政策措施就可以降低國債發行成本,支持擴張性財政政策作用。如果國債市場對國債需求不旺,中央銀行完全可進場(二級市場)購買國債,活躍國債市場、降低國債成本。在這方面中國有足夠的政策空間。
第十三,由於通脹形勢的惡化,美國在2022年將開始退出已經執行12年的極度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美國的政策調整將對中國的國際收支造成不利影響,人民幣貶值壓力會有所上升,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將會受到一定影響。但是,由於美聯儲政策調整將是漸進的,相信2022年中國的外部經濟環境不會發生急劇變化。中國只要允許人民幣匯率保持足夠彈性、對資本的跨境流通保持必要的監管,外部環境的變化應該不會對中國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造成很大影響。
第十四,關於2022年的經濟增速,市場似乎普遍認為應該是5.5%。對此,我比較認同。一方面,我們畢竟受到疫情的嚴重衝擊,經濟增速低於2019年是正常的。另一方面,我們有採取更具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的餘地,可以實現較高的經濟增速。但是也有必要強調實行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是要有條件的。一是項目儲備到底足不足?如果事先沒有預做準備,可能找不著項目。二是地方政府是否做好了思想、組織上的準備。如果沒有,地方政府將難以承擔組織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的任務。總結2008年“四萬億”的經驗教訓,我們不能操之過急。
毋庸贅言,宏觀經濟政策的成敗,不僅在於設計,而且在於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度環境、政治生態。由於中央已經提出“穩增長”的大政方針,對於2022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前景,我們有理由感到樂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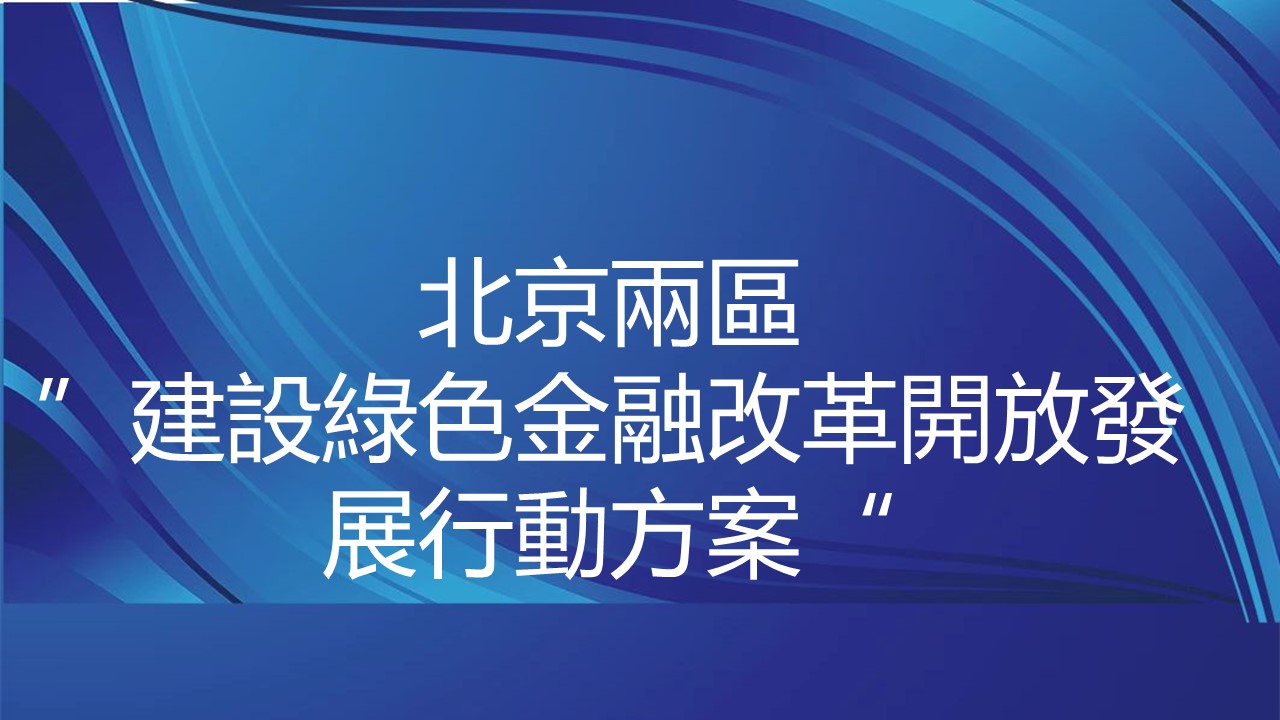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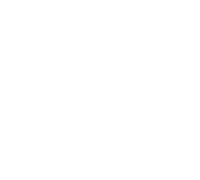




請先 登錄後發表評論 ~